人文書店,如何經營理想?
來源:
聯商網
2009-06-11 10:39
人文書店,如何經營理想?
提到巴黎,我們會想到“莎士比亞書店”;說到紐約,“高談書集”無法避之不談;徜徉于臺北街頭,“誠品”書店很適合流連忘返;而在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已然成為自由藝術的代名詞。
一家書店,成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標,這樣的事情無關噱頭,只關乎一種心境——止水般的和浪潮般的讀書人的心境。這樣的書店勘透了書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如同眼睛和世界之間的關系,讓我們在多年后,仍能回憶起手指劃過書頁的種種欣喜與感動。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批帶有人文理想的民營書店到今天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它們曾經并將繼續影響不同城市中人們的生活和閱讀,城市也因為它們的存在而別具意義。
緣 起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給此類書店冠名,獨立書店、學術書店、人文書店、專業書店等等名詞似乎都單薄得難以將其涵蓋。貴州西西弗書店創始人之一薛野將其劃歸為由第二代書商建立起來的帶有人文理想與社會關懷的民營書店。他們的創辦者大多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被鄧小平南巡所激蕩,熱愛閱讀,嗜書如命,當能將愛好與事業相結合之際,民國知識分子在書業界既能“安身”、又能“立命”的時機似乎再次來臨,奮不顧身地投身書海也就成為第二代民營書業人的必然選擇。
另一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知識界開始分流,一部分知識分子從體制內走到了體制外,文化人選擇開書店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與其他書店不同的是,這些書店承載著思想交流的責任,是店主們自我表達的方式,在定位上不約而同地趨向于人文、社科、學術。他們在不同的城市里代表著滿懷激情的、新鮮的、前衛的思想和文化,不為商業、盈利所困擾,有的只是純粹的理想與情懷。
正如同福建曉風書屋總經理許志強所說,為了能看到最新的圖書,為了給朋友在被每本圖書激動和感動之余提供相互交流與傾訴的場所,所以有了曉風;也正如同王煒生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成立風入松的愿望就是讓翻譯書、寫書的學者有一個出售作品的地方,讓需要這類書的同好能夠買到這些書。或許這些并不是每個人文民營書店創立的緣由,但它們代表著一批有情懷的民營書店最樸素的初衷。它在每個有抱負的愛書人心里悄然生發,十年風雨兼程,走到了大書城林立的21世紀。
沖 突
在物質誘惑越來越明目張膽的今天,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在競爭對手越來越強悍的今天,在書業態勢尚不明朗的今天,這一批民營書店能否在文化理想與經濟效益之間找到平衡點?這是我們在采訪時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有人說,人文學術書店在精神上的發展脈絡是當代知識分子精神生命的一個側面,但在經營理念上相對傳統書店而言是從零開始,在一段時間之后,幾乎都要面臨追求經濟效益與堅守文化理想的艱難抉擇。是堅持自我還是向商業妥協,這似乎成為書店“魚與熊掌能否兼得”的一個永恒命題。
而魚與熊掌的沖突導致的結果無外乎三種。
其一,或因經營不善,或因殘酷競爭,或因喜好變化,總之,在這場理想與商業的爭奪戰中,書店徹底敗下陣來,注定成為某個圈子里的人在茶余飯后偶爾唏噓的話題。比如成都卡夫卡書店,比如廣州的樹人書店、七星書社,這兩家上世紀90年代初創辦的書店在學而優書店總經理陳定方的記憶里,是廣州小有影響的人文書店,后者的老板是出版編輯出身,身兼詩人與評論家身份。現如今,陌生的愛書人在慕名尋訪未果之時,只能在慨嘆一聲“人,詩意地棲居”后,揮袖而去。薛野則認為有出有進正是行業生生不息的體現及業界生態的多樣性所在。
其二,向商業妥協,人文、學術、社科的定位徹底轉變,轉向做大做強,其前景卻難以預料。龍之媒廣告文化書店董事長徐智明告訴記者,相對大書城所追求的投入產出,利潤并不是此類書店追求的惟一目標,在理想與商業之間權衡,如果單一地往商業方向靠攏,中小書店反而會走向死胡同。
其三,找到文化理想與經濟效益之間的平衡點,既不失“店格”,又擁有了持續發展能力,萬圣、季風、學人、精典、西西弗、學而優、曉風、先鋒、龍之媒等書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用薛野的話來說,學術人文書店在店主的人文理想與經濟效益之間的沖突并不會惡化,聰明的經營者可以在理想與務實之間找到平衡,從而成為理想主義的實干者。
然而,羅馬城不是一夜建成的,理想的實干主義者也并非一天練就,其中或許有過失敗的慘痛,有過血淚的教訓。比如西西弗、萬圣和國林風三家書店聯合在北京開辦的學術圖書中盤——廣域公司,最終以失敗告終,萬圣書園總經理劉蘇里事后總結,獨立書店雖然需要自己的中盤,但其理念超出了當時民營書業在管理、信息流、物流等方面的水平。
展 望
個性書店所占的市場份額微不足道,因為它們大多很難用商業手段大批復制。有觀點認為,學術書店作為一種生意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成立的,因為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其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但是為什么能堅持下來?這正是因為書店經營者在經濟因素之外,賦予了書店更多需要表達的價值觀念,而這正是其生存的真正核心價值所在。
因此,在倡導人文閱讀理想的同時,走上書業前臺的人文獨立書店一直在解決這樣一個難題:將文化活動和商業活動從對立的兩極轉變為相輔相成的二元。萬圣書園與房地產的結合或許屬于此類。
上海季風書園總經理嚴搏非曾經這么說過,圖書是很有個性的商品,每一個都不一樣,它承載的不僅是文字和圖畫,而且是思想和精神,所以在這個行業里,盡管也有資本的橫行,但還是可以有百年老店,也可以有百年小店。“民營店要守住自己的初衷并不難,依我想,只要認認真真地,還是把書店當做書店來做。”他說。
展望書業,此類獨立人文學書書店在數量上應該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大,其存在的最大意義之一就在于給同業者提供了反省自身的機會與探討理想與責任的可能。用書業生態系統來理解的話,每個物種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不應該用體積、規模、大小等來衡量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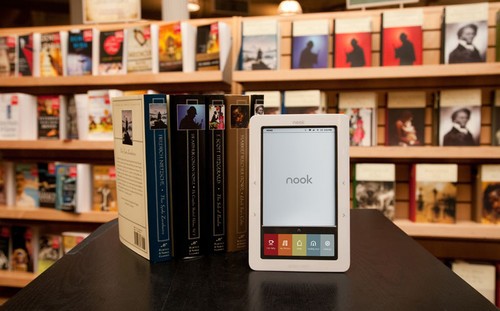





發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