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在書店團結起來
來源:
于堅
2008-04-30 15:14
書店面積不大,就是十平方米左右。店主馬力是個年輕人,喜歡詩、哲學、傳記、電影、人類學、音樂文學、繪畫什么的。他的趣味有點波西米亞,總是能找到那些非主流的書籍。我經常去買一摞書,作為有40年閱讀史的讀者,我自信看書已經是火眼金睛,在馬力的書店里,入得我眼的書經常有。他才30歲出頭吧,眼光不俗。
現在出版書籍太隨便了,說圖書業已經成了垃圾制造業,一點也不過分。這是一個便宜的時代,只要有得錢掙,怎么都行,似乎已經沒有什么比錢更貴的東西了。別看現在書這么多,真正的讀者寥若晨星,而且越來越少,看電視、上網的越來越多,繼續看書的是少數沒落貴族。昆明現在大多數所謂的書店,完全沒有品位,就是一百貨商場,進去一趟令人暈頭轉向。這是圖書市場而不是書店,就像花卉市場永遠不是花園一樣。
馬力的書店有點像巴黎那些形形色色的小書店,巴黎很少有巨大的什么都不放過的書店,書店都是有老板獨特的個人趣味的,為相應的老讀者服務。賣舊書就是賣舊書,賣老唱片就是賣老唱片,賣攝影作品就是賣攝影作品,時尚雜志再怎么賺錢,你就是白送他他也不賣的。
昆明大部分書店都賣一樣的書,去一家就可以了。馬力的小書店是個例外。現在淘書可不容易啊,想想那些拿著個耙子、背著籮筐在臭氣沖天的垃圾山上刨來刨去的人們,淘書也大抵如此。熱愛某件事情,不從贏利與否的角度出發、只是一心一意喜歡它、用心做好它的人相當少,中國恐怕已經是全世界這種人最少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國可以說是世界的沙漠。無數人在干他們內心深惡痛絕、令他們精力疲盡、惶惶不可終日的事情。
馬力的書店開了四五年了,他旁邊的許多店經常易貨,今年賣鹵豬蹄,明年賣南韓時裝,后天修奔馳,什么掙錢賣什么,走馬燈快得連招牌都懶得換了,賣文具的招牌下面在賣著火鍋。馬力巋然不動,賣書,還是賣書,且決不擴大經營規模。他的書店幾乎沒有什么贏利,還要給讀者打打折,也就剛夠糊口。賣書是他的一個玩場,趣味、存在感。清貧但快樂,每次見他,都是身居天堂的樣子,就像我,30年來,寫詩而已。
在昆明,麥田書屋是我最喜歡的書店,經常去,閑坐,隨便翻翻,馬力在書店里支了舊沙發,整天放著音樂,就像一個家。我揀一堆書坐下來,慢慢翻,經常覺得,這些書的作者,必然也是這個書店的常客。這家書店就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博爾赫斯和他的朋友也會找到它的。這樣的書店在昆明太少,在整個中國都太少,如果錢局街一條街都是這樣的書店,昆明就太好玩了。我就是那種傳說中所謂“不是在去書店的路上,就是在從書店回家的路上” 的家伙,我與書店的歷史可以說是一段傳奇,昆明哪一家書店我不知道啊,我甚至記得那些老店員青年時期的綽號。
馬力的小書店是玻璃門,外面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一進去,世界立即安靜下來,似乎在等著文字的最后審判。看著外面的日光流年,我有時候靈感忽至,就要個紙條記下。偶爾在書店里遇到我的讀者,我總是在馬力的書店遇到我的讀者,不是別處。這令我意識到我在為哪些人寫作,而以前我不太知道誰在閱讀它們,現在我知道一點——他們喜歡馬力的書店。
馬力很年輕,長得像個蒙馬特高地咖啡館里的詩人,輕聲說話,蒼白、有點迷惘,像某種長在人群中的大麻。我們都是大麻,被上帝種植在人世間。有時候我們聽點西藏音樂。我過去很忌諱這一套,書店、咖啡、先鋒派電影、凱魯雅克、牛仔褲、列儂、激浪派、布魯斯……我愿意把這些有點超凡脫俗、有點“裝佯”的私人趣味暗藏在我生命的暗室里。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在一個庸俗和拜物就像暴力的一樣令人窒息的時代,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相當重要,這個“佯”是很有必要公開地裝裝的,我們就是要超凡脫俗,就是要“舉世皆濁獨我清”,就是要“富與貴,于我如浮云”,就是要“道不同,乘桴浮于海”。
我們這些自得其樂的寫點詩的、畫點畫的、搞點音樂的、拍個紀錄片的、讀書如饑似渴的……其實已經被世界開除成為一個少數民族,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在書店團結起來,在莫扎特的音樂中團結起來,在咖啡館團結起來,在詩歌朗誦會團結起來,在前往西藏的途中團結起來,在秋天的月光下團結起來,在老鷹的翅膀下團結起來,在大地上團結起來,在日益喪失的故鄉團結起來……這是所有不愿意同流合污者的宿命,這是一種獨行特立的生活方式,就像過去時代文人日夕相伴的文房四寶、松竹梅蘭。
忽然,麥田書屋就被拆掉了。綠化城市,規定必須完成X萬平方米,馬力的書店被計算在內。書店位于兩個建筑物之間,走三步就到頭的一點空間,人家要綠化。馬力一籌莫展,只有隨遇而安,逆來順受,另尋鋪面。拆除的限期就要到來,我那天最后一次去買書,心情相當糟糕——對于一個讀書人,還有比一家自己所愛的書店關門完蛋更痛心的事情么?
馬力后來在文林街文化巷內師大附小后門那里又找到一處房子,重新開門。只是租金相當高,維持下來更困難;而且許多老讀者,再也找不到這個家了。他的書店又要再次從零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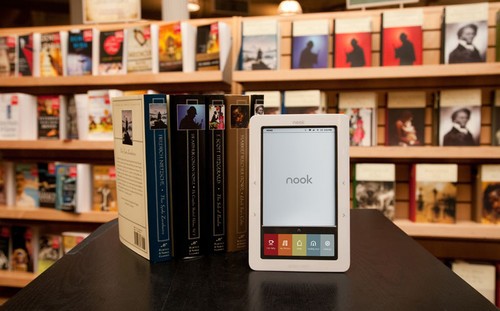





發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