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艱難地存活曲折地發展
有論者稱“二樓書店”是“香港一片獨特的書業氛圍”,我對此是深以為然的。
香港“二樓書店”的出現,大概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吧。猶記我1990年春首次到香港大學開會,會后在方寬烈先生和已故的陳無言先生陪同下走訪香港的大小書店,最使我感到新鮮特別的就是“二樓書店”。固然像三益書店、波文書局這樣的老牌舊書店仍是一樓底商,但旺角的新亞書店、彌敦道的實用書局以及現在在大陸已大名鼎鼎的中環士丹利街的神州舊書文玩公司等等,都已經是“二樓書店”了。跟著方、陳二位前輩進得樓門,搭乘狹小的老式電梯或從七轉八彎昏暗的樓梯拾級而上,去遨游未知的舊書陳刊的海洋,我的心情是緊張而又刺激,這簡直是一次次從未體驗過的求學探險。新亞書店門口竟然懸掛沈從文的章草條幅,實用書局老板龍良臣上世紀40年代末曾主持出版過聶紺弩不少著作的求實出版社,這都是我萬沒想到的。每當我雙手烏黑,拎著大包小包的舊書離開書刊堆積如山的店堂,走到陽光明媚的大街上時,我對這些“二樓書店”真是充滿了感激。
“二樓書店”的存在,確實是香港舊書業的一道風景。當時的香港,是內地、臺灣、香港、澳門乃至東南亞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出版的中英文書刊的聚散地,至今也仍然是,這樣的聚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二樓書店”才得以實現的。長期以來,“二樓書店”為香港和海內外讀書人所提供的稀見資料,指示的治學門徑,是便捷的,充分的,也是數量巨大的。至少在我,有許多夢寐以求的舊書,不少研究題目的靈感,就是從逛“二樓書店”得來。如果要細數這些年來我在香港“二樓書店”所遇到的驚喜,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的,暫且按下不表。
大概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始,我每次到香港都會發現,由于租金的日益昂貴,再加上閱讀環境的逐步邊緣化,“二樓書店”已處于不斷變動之中,而且變得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急管哀弦”(張愛玲語)。這些我所熟悉的店面簡陋的“二樓書店”,有的關閉了,有的縮小了,有的搬遷了,有的“高升”了(“升”到了四樓、五樓甚至更高),更多的仍在堅持,苦苦地堅持。不僅是舊書店,新書店尤其是個體或合股的小型新書店也紛紛加入“二樓書店”的行列。在我看來,香港“二樓書店”的新舊歸屬往往是相對的,我不止一次地在舊書店里見到剛出版不久的內地“新書”,又經常在新書店里翻出十多年前甚至更早出版的全新的港臺“舊書”。
這就不能不說到羅志華兄和他的青文書屋了。
青文書屋是香港“二樓書店”的一個代表,一個縮影,原址“灣仔莊士敦道214-216號三樓B座”,以經營文史哲類書刊而聞名。這莊士敦道是港島一條車水馬龍的大馬路,青文書屋建立之初就占了“地利”之便。已經有有心人梳理了青文書屋的盛衰史,羅志華兄并不是青文的創始人,但自從他接手起,青文就邁入了一個令香港和大陸讀書人刮目相看、留連忘返的新階段。我已記不清最初是怎么去青文的,應該是小思老師的介紹,第一次也應該是她帶我去的,以后我每到香港就非去青文不可了。我在青文買了不少書,青文也即羅兄精心策劃編印的“文化視野叢書”更差不多悉數購置,還一直對“心猿”所著長篇《狂城亂馬》到底出自何人手筆感到好奇。與別的“二樓書店”店主不同,羅兄會根據讀者的愛好和興趣主動推薦新書。不過,由于他普通話不好,而我又不懂粵語,我們的溝通交流并不順暢,有時還要借助“筆談”,現在回想起來也算是難得的經歷。
羅兄十分低調。記得我有次向他索取名片以便通信聯系,他順手取了一張“青文書屋取書單”給我,上面印有書店地址和聯系方式,他又隨筆一揮簽上了大名。這張折疊好的“取書單”我一直保存著,它勾起了我又一段溫馨的回憶。2001年4月,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本《張愛玲典藏全集》。半年之后我到港開會,照例去青文書店看書(這也是我最后一次光顧青文),羅兄知道我研究張愛玲,告知店里還剩下一套,建議購買,我因臺灣“遠景”沈登恩兄已經送我而作罷。返滬后與友人邱兄談起,他喜好豪華本,極想收藏這套裝幀堪稱考究的張愛玲“全集”,于是我馬上發傳真詢問羅兄;也是邱兄運氣好,這套書竟然還未售出,羅兄答應為我留著,為免郵寄受損,還主動提議他來滬時攜來。這真太麻煩他了,使我很不好意思,但也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又過了半年,已是2002年盛夏,羅兄果然攜書蒞臨滬上,但他忙于四處找書,無法與我見面,我是按約定時間到他借住的友人處付款取書的。除了書價優惠,運輸手續費之類他也分文不取,再次使我很不好意思。原以為以后還有機會當面向羅兄申謝,沒想到就此天人永隔了。
羅志華兄離奇地因店內書架倒塌而英年早逝,成了香港文化界的重大事件,在內地也引起了強烈反響。莊士敦道的青文雖然不得已而被迫“結束”,但羅兄本來是不折不撓,積極準備“再出發”的。真是痛惜啊,如果不發生那悲慘的一幕,羅兄的青文復興計劃已經啟動,新青文也早應開張,我們也許又會在擁擠的書堆中“筆談”暢敘了。羅兄的離去,悲壯地證明他的生命已完全與書融為一體,他用生命殉了他的書!
香港的“二樓書店”應以有羅志華兄這樣敬業、這樣癡迷書籍的主持人而自豪。多少年后,當人們要研究香港“二樓書店”史時,一定不要忘記羅志華這個名字。羅兄走了,香港的“二樓書店”仍艱難地存在著,曲折地發展著。去年十一月,我到深圳參加“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本書”評選活動,承主辦方美意,與北京止庵兄、楊小洲兄等愛書的朋友作香港“二樓書店”一日游,在旺角的新亞、樂文、學津、田園書屋、香山書社等“二樓書店”消磨了整整一個下午,各取所需,直到華燈初上才手提肩扛,滿載而歸。我高興地發現睽隔三載重來,“二樓書店”仍在頑強地維系著香港的一縷書香。當今網上購書和拍賣已經如此發達,我還能在這些有特色的“二樓書店”淘到中意的舊書和新籍,價格又公道,實在是意外的收獲。為“二樓書店”獻出了生命的羅志華兄如果泉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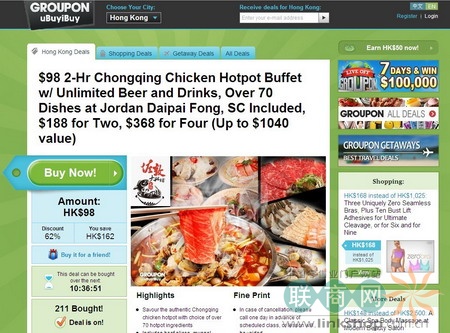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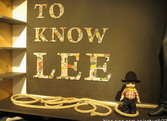

發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