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麥肯錫城市群方法分析中國城市
用麥肯錫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去區(qū)別對待中國的不同城市,將800多個中國城市劃分為若干個城市群,關(guān)注它們在收入水平、地理位置、城市間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和貿(mào)易往來諸多方面的區(qū)別和差異、以及城市中消費者共同的消費態(tài)度和偏好等。
廣州和深圳有著很多共性,但這兩座同處一省、駕車距離僅為3小時的城市在人口構(gòu)成、語言和消費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別卻不亞于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差異。深 圳居民中,4/5為外來務(wù)工人員,大多數(shù)年齡在35歲以下,他們說普通話或自己的方言,習(xí)慣在酒吧喝一杯。而在鄰近的廣州,外來人口只占1/4,人口年齡 偏高,主要說廣東話,習(xí)慣于與家人一起去餐館喝茶。
很少有跨國公司會在法國和德國市場運用同樣的策略,但似乎很多公司在中國卻正是這么做的。它們專注于培植最大的市場(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以及類似南京的較大的二線城市),而忽略了中國數(shù)以百計的城市之間的差別。
中國的市場如此之大、各地增長的速度如此千差萬別,對它們進行優(yōu)先排序是不二的選擇。中國的800多個城市中有200多個人口超過100萬(在整個歐洲,人口超100萬的城市只有35個)1。另外,中國還有數(shù)百個人口在10萬級的城市。
現(xiàn)在,很多在華公司對中國城市仍采用逐個管理的方法。然而,通過總結(jié)它們的工作經(jīng)驗,以及我們對中國消費者的研究2,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種更有效且更合算 的管理方法,即麥肯錫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簡單的城市層級和地理區(qū)域來劃分中國城市,而將800多個中國城市劃分為若干個城市 群。這些城市群少則包括2個城市,多則包括約70個鄰近的城市。決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還包括城市之間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和貿(mào)易往來,以及城市 中消費者共同的消費態(tài)度和偏好。
用麥肯錫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能幫助企業(yè)定義戰(zhàn)略愿景、優(yōu)化資源配置,跟蹤業(yè)績。與逐個管理城市的方法相比,用城市分群的方式更能在 廣闊地域范圍內(nèi)實現(xiàn)銷售隊伍、分銷渠道、供應(yīng)鏈以及營銷的協(xié)同效應(yīng),更有實效性和成本效益。同時,比起將中國城市簡單分成幾個地區(qū)的做法,用城市分群的方 式能將工作做得更細(xì)。
麥肯錫ClusterMap:從城市層級到城市群
麥肯錫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將中國城市分為22個城市群,每個城市群圍繞1到2個中心城市發(fā)展。為了確保這種方法是可行并適用的,所有的衛(wèi)星城距離1個中心城市不超過300公里,并且每個城市群的GDP都超過中國城市總GDP的1%(圖表1)。

在這22個城市群中,我們將其中的7個定義為“超大型”。在2008年,其人口總數(shù)在1900萬到5500萬之間,且每個城市分別占中國城市GDP的5%~12%。另有10個城市群被定義為“大型”,其人口總數(shù)在1300萬到3900萬之間。
麥肯錫城市群(ClusterMap)涵蓋了中國815個城市中的606個,占中國城市人口的82%,預(yù)計到2015年將占據(jù)城市GDP的92%。
各家企業(yè)最終確定的城市群數(shù)量可以有所不同。有些公司或為了擴大分銷中的規(guī)模經(jīng)濟,或因為某些城市群中的類似的媒體觀看習(xí)慣和對媒體渠道的偏好,而 將一些城市群合并。另一些公司則可能因為某些城市群內(nèi)差異(比如競爭狀況或消費習(xí)慣),需要運用不同的戰(zhàn)略,而將一些城市群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小城市群。
城市群劃分的4個考量因素
在繪制城市群地圖之前,我們從以下4個維度分析了中國的815個城市3:產(chǎn)業(yè)構(gòu)成、政府政策、人口特征以及消費者偏好。
產(chǎn)業(yè)構(gòu)成
在繪制中國的城市群時,我們研究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即經(jīng)濟的導(dǎo)向是服務(wù)業(yè)、制造業(yè)還是農(nóng)業(yè)),以及一個城市群內(nèi)的城市之間在經(jīng)濟活動和貿(mào)易往來方面的一體化程度。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濟聯(lián)系決定了人口構(gòu)成、收入水平,并最終決定了城市群內(nèi)的消費者偏好和行為。
端對端的產(chǎn)業(yè)價值鏈的形成是促進城市群內(nèi)經(jīng)濟活動一體化的一個因素。例如,中國最大的國內(nèi)汽車生產(chǎn)商上汽集團的成立及其與美國通用汽車成功合資,帶動了在上海郊區(qū)和周邊城市形成一個綜合性的汽車零部件供應(yīng)商網(wǎng)絡(luò),為上海贏得了“中國底特律”的稱謂。
另一個促進城市群內(nèi)的城市間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因素是某些商業(yè)活動在各城市之間的分布。例如,許多高科技企業(yè)在上海設(shè)立行政管理部門,而將制造部門放在張江高科等開發(fā)區(qū)或昆山等周邊城市。
政府政策
中國城市的發(fā)展體現(xiàn)著強大的政府力量。最近幾十年中,中央和各省市制定的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和人口政策加速了城市群的形成。1989年,中國政府宣布了鼓勵 大城市之間以及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經(jīng)濟合作的多項政策。例如,在2005年開始實行的十一五規(guī)劃中,中國國務(wù)院確定了11個城市群,旨在推動經(jīng)濟增長、加 強交通運輸聯(lián)系,并影響人口流動。跨市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和開發(fā)項目也加強了城市之間的經(jīng)濟和交通聯(lián)系。
其它還有一些政策針對具體的地區(qū),有著非常具體的目標(biāo)。例如,旨在將內(nèi)蒙古打造成“亞洲乳業(yè)之都”的政策:隨著該地區(qū)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逐步轉(zhuǎn)向以乳制品的生產(chǎn)和銷售為主要的經(jīng)濟推動力,越來越多的人被吸引到該行業(yè)就業(yè),從而獲得類似的工資,因而很可能形成最終類似的消費偏好。
人口特征
當(dāng)?shù)厝丝诤屯鈦砣丝诘谋壤⒛挲g層構(gòu)成、收入水平以及家庭儲蓄率都是我們用來定義城市群的關(guān)鍵人口因素。
大批外來人口涌入到城市中生活,中國的城市面貌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1990年至2005年之間,有1億外來人口涌入了城市。到2030年,預(yù)計將有10億人口生活在中國的城市中4。
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對各個城市群的影響千差萬別,因而形成了各城市群的個性差異。深圳有86%的人口來自外省,他們說普通話(也說自己的方言);而 73%的廣州居民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主要講廣東話。由于外來人口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深圳比廣州年輕很多:55%的深圳居民年齡在20~34歲之間,而這個年 齡層的人口只占廣州居民總數(shù)的35%。19%的廣州居民年齡在49歲以上,而在深圳這一比例只有7%。
消費者偏好
我們的研究表明,城市群與消費者行為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guān)性。2005年,我們開展了第一次中國消費者調(diào)查,在14個最大的消費者特性差異中,有9個 (如品牌忠誠度或支付溢價的意愿等)可以由該城市歸屬于的城市層級、而不是其歸屬某個地域上相鄰的群體來解釋。然而,我們2009年第一季度進行的調(diào)查發(fā) 現(xiàn),在這14個特性差異中,有11個應(yīng)當(dāng)用城市群來解釋(圖表2)。

我們注意到,中國各城市群消費者的行為存在很大差異。例如,52%的上海城市群消費者青睞名牌產(chǎn)品,而這一比例在廈門-福州城市群(包括潮州、汕頭、石獅等城市)中只有36%。
消費者對產(chǎn)品特性的偏好也很不一樣。例如,深圳城市群的消費者青睞輕、薄的數(shù)碼相機,而廣州城市群的消費者偏愛有大顯示屏的機型。
不同城市群中的消費者對媒體的偏好也大相徑庭。例如,“中原城市群”(包括鄭州、洛陽、開封等城市)中95%的消費者喜歡看中央臺。而62%的上海 城市群消費者喜歡看本市的電視節(jié)目。對各地消費者看電視習(xí)慣的深入了解,有助于那些在電視廣告中投入甚多的消費品公司更有效地分配他們在不同城市群之間的 媒體投資支出(圖表3)。

我們發(fā)現(xiàn),在城市群的形成過程中,各因素之間互相影響,形成一種良性循環(huán):政府政策塑造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影響人口構(gòu)成,人口構(gòu)成又被反映在消費者行為中。時間一長,這些因素增強了城市間的聯(lián)系,并促使特定城市群內(nèi)的消費者行為逐漸趨同。
制定以城市群為基礎(chǔ)的戰(zhàn)略
企業(yè)在繪制出城市群之后,需要確定應(yīng)瞄準(zhǔn)哪些城市群,以及在每個城市群運用什么樣的策略。在這一決策過程中,需要實施4個關(guān)鍵步驟:尋找增長最快的城市群、對目標(biāo)城市群進行優(yōu)先排序、設(shè)定城市群層面的發(fā)展愿景、以及定義戰(zhàn)略性“原型”并量身定制市場策略。
尋找增長最快的城市群
2008年~2015年之間,中國將有7500萬城市家庭加入中產(chǎn)階級(家庭年收入在5萬~12萬元之間)的行列。中國的人均消費將從2008年的 1.34萬元上升至2015年的1.7萬元人民幣。屆時,城市人口消費總額將達(dá)到13.3萬億元(1.94萬億美元)5。中國將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后的世 界第三大消費市場。
但財富的增長在中國并不平均,因此,了解哪些城市將呈現(xiàn)最有吸引力的增長機遇對投資的優(yōu)先排序至關(guān)重要。例如,合肥2015年的中產(chǎn)階級占比預(yù)計將迅速從2008年的35%增長至67%,而同一時期,杭州的中產(chǎn)階級只會從73%略微上升至75%。
中產(chǎn)階級增速的差異也會反映為消費增長速度的差異。中國最大的100個城市中,有25個的消費總值有望在2008年~2015年之間翻一番。這些城 市包括北京、煙臺、威海和松原。同期,包括上海、武漢和湛江在內(nèi)的25個城市的消費有望增長50%~100%。即使一些城市的增長率為一位數(shù),其增長速度 還是會超過全球增長水平,從而帶來可觀的商業(yè)增長機遇。
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加入中產(chǎn)階級行列,他們有能力負(fù)擔(dān)除了食品、醫(yī)療保健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越來越多的其它物品。他們的支出目標(biāo)轉(zhuǎn)向汽車、家用 電器、個人電腦和個人護理用品,以及娛樂或奢侈品等非必需品。例如,杭州2008~2015年的汽車需求量預(yù)計將出現(xiàn)14%的年均增速,而合肥的汽車需求 量更則將實現(xiàn)36%的高速增長。
對目標(biāo)城市群進行優(yōu)先排序
隨著低層級城市的發(fā)展,僅僅關(guān)注高層級城市的策略正變得日益缺乏成本效益。不僅如此,這些策略還將投資風(fēng)險集中在協(xié)同效應(yīng)低、缺乏增長后勁的城市 上。麥肯錫的ClusterMap幫助企業(yè)專注于數(shù)量有限的優(yōu)先城市群上。例如,在廈門和福州或周邊推動業(yè)務(wù)增長之前,先投資于廣州周邊城市擴大業(yè)務(wù),業(yè) 務(wù)發(fā)展速度可能更快、且成本更低,因而投資回報率也更高。
在那些企業(yè)已經(jīng)擁有牢固地位的優(yōu)先城市群中,它們可以擴建規(guī)模,在多個城市共享分銷基礎(chǔ)設(shè)施、供應(yīng)鏈和銷售隊伍,充分利用和共享其對該地區(qū)長期以來 積累的專業(yè)知識和資源,還可以更好地利用電視收看的協(xié)同效應(yīng)。例如,在以廣州為中心的城市群中,電視觀眾喜歡收看主要以廣東話播音的省級電視臺節(jié)目。一家 個人護理用品公司通過在城市群層面與零售商和物流提供商談判中取得更優(yōu)惠的貿(mào)易條款,并發(fā)現(xiàn)了在全國性電視臺打廣告具有更好的效果,因而削減了在本地電視 臺的廣告投入,該公司的凈利率因此翻了四番。
企業(yè)還可根據(jù)一系列因素在所選城市群中做出營銷選擇。比如說,是走遍布城鄉(xiāng)的百貨公司和大賣場等現(xiàn)代化渠道,還是走傳統(tǒng)的夫妻店零售渠道;是在乎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還是關(guān)注他們對價格的敏感度;以及消費者嘗試新產(chǎn)品的意愿等等。
此外,企業(yè)在選擇瞄準(zhǔn)哪些城市群的同時,還需要在城市群內(nèi)部的各城市、分銷渠道和單一銷售網(wǎng)點之間做出選擇。
設(shè)定城市群層面的目標(biāo)
企業(yè)在考慮在多個城市群追求市場領(lǐng)導(dǎo)地位時,需要考慮當(dāng)?shù)馗偁幍奶攸c和白熱化程度。中國許多地區(qū)性企業(yè)和跨國公司盡管在某些地區(qū)建立了據(jù)點,但是, 其中一些地區(qū)對公司利潤做出的貢獻(xiàn)與其規(guī)模很不相稱。雖然全國性規(guī)模在某種程度確實重要(尤其是利用全國性電視臺打廣告的品牌),但地區(qū)性規(guī)模卻更有意 義。許多品牌即使在全國范圍內(nèi)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但它們?nèi)匀荒塬@得地區(qū)性的成功。
以受中國人喜愛的白酒為例。除了少數(shù)奉行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激進策略的超高端品牌外,大部分白酒品牌在某個城市群或地區(qū)擁有高達(dá)40%~50%的市場 份額,但其全國市場份額卻僅僅只有2%~3%。這種現(xiàn)象在全國20多個城市群、各個品類中都十分普遍。例如,一家國內(nèi)食品和飲料公司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中 國南方的少數(shù)城市群中,在當(dāng)?shù)亟⒘耸袌鲱I(lǐng)導(dǎo)地位,其市場份額高達(dá)40%以上。但它在中國其他地區(qū)的份額卻很小,或根本沒有。
企業(yè)需要根據(jù)城市群的內(nèi)在吸引力以及自身在該地區(qū)開展競爭的能力,調(diào)整自己的目標(biāo)。一旦根據(jù)麥肯錫ClusterMap的方法選定了優(yōu)先發(fā)展的城市群,企業(yè)就應(yīng)制定合乎情理有防守空間市場份額目標(biāo),例如,40%的市場份額。
定義戰(zhàn)略性“原型”并量身定制市場進入策略
針對中國的22個或更多的城市群,制定各自不同的戰(zhàn)略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wù)。量身定制產(chǎn)品、培訓(xùn)銷售隊伍、管理分銷渠道和設(shè)計營銷活動,以適應(yīng) 中國不同城市群中的各類消費者,會迅速耗盡預(yù)算,分散管理層精力。因此,為了對資源進行優(yōu)先排序和集中利用,企業(yè)應(yīng)該根據(jù)這些城市群的共同特點和自身的戰(zhàn) 略目標(biāo),將它們歸納為三種或四種有代表性的“原型”,并為每一種“原型”制定具體戰(zhàn)略。
一家食品和飲料公司根據(jù)自己在具體城市群的競爭地位和對這些城市群的策略目標(biāo),將目標(biāo)城市群分為4種“原型”。“據(jù)點型”城市群是指那些具備相當(dāng)規(guī)模、發(fā)展迅速、企業(yè)已在那里取得了領(lǐng)先地位、且需要不惜成本捍衛(wèi)勝利成果的市場。
“志在必得型”城市群是指目前尚未取得市場領(lǐng)先地位,但由于其市場規(guī)模的龐大和增長速度快,企業(yè)希望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城市群。在“志在必得型”城市群里,企業(yè)需要部署新產(chǎn)品解決方案和新的溝通策略,以說服消費者改變原有品牌偏好。
“有前途型”城市群是指盡管在具體品類上的人均消費量可能依然不高,但其預(yù)計增長率將遠(yuǎn)遠(yuǎn)超過市場平均水平的城市群。在這些城市群中,企業(yè)可以將營銷資金投入在消費者培育上,以便提高消費者對該品類產(chǎn)品相關(guān)優(yōu)勢的認(rèn)知程度。
其余城市群則歸類為“觀望型”。它們或者是規(guī)模過小,或者是競爭過于激烈而沒有被選擇為優(yōu)先開拓的城市群。公司應(yīng)該盡可能減少在這些城市群的投入,只需確保其品牌在消費者中的知名度,以及消費者能夠通過分銷渠道獲得其產(chǎn)品。
當(dāng)然,在一家公司奏效的方法未必能在另一家公司行得通。上述食品和飲料公司最后歸納了4個城市群“原型”,而一家個人護理產(chǎn)品公司則根據(jù)消費者是否 喜愛傳統(tǒng)的固體肥皂、是否使用液體肥皂,或者是否正在從使用固體肥皂轉(zhuǎn)化為使用液體肥皂,而確定了3種“原型”。該公司開發(fā)了截然不同的產(chǎn)品組合、制定了 截然不同的品牌和營銷戰(zhàn)略、分銷模式和銷售戰(zhàn)術(shù)。
使用平均水平已經(jīng)不再能夠描繪出中國消費者的真實全貌。利用麥肯錫ClusterMap,企業(yè)可以了解關(guān)于消費者行為和消費模式的異同,并獲得對今 后幾年消費模式可能變化趨勢的具體認(rèn)識。無論是對準(zhǔn)備進入中國市場的企業(yè),或是正在通過發(fā)現(xiàn)新市場以加速發(fā)展的企業(yè),還是希望繼續(xù)提高現(xiàn)有業(yè)務(wù)利潤率的企 業(yè),這一認(rèn)識都可以幫助他們制定更加有效的戰(zhàn)略。
作者簡介:
安宏宇(Yuval Atsmon)是麥肯錫上海分公司副董事;狄維瑞(Vinay Dixit)在上海分公司領(lǐng)導(dǎo)麥肯錫解讀中國(Insights China)業(yè)務(wù)部門的工作;馬思默(Max Magni)是麥肯錫上海分公司董事、大中華區(qū)消費者咨詢業(yè)務(wù)負(fù)責(zé)人。
作者謹(jǐn)向為本文所依據(jù)的研究做出貢獻(xiàn)的澤沛達(dá)、王磊智、Derek Chang 、鄭茵欣、張悅以及前雇員丁穎和張曉穎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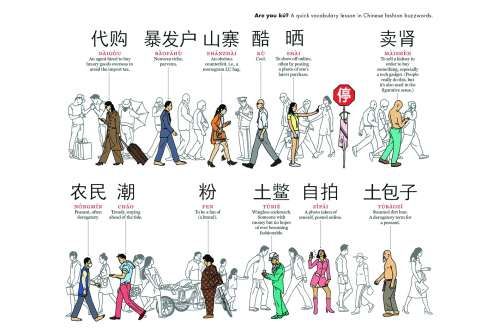
發(fā)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