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日本零售商業(yè)不振,大眾收入低、負(fù)擔(dān)重

出品/聯(lián)商專欄
撰文/聯(lián)商高級(jí)顧問(wèn)團(tuán)成員潘玉明
進(jìn)入2022年,觀察日本零售動(dòng)態(tài),總體依然不振,源自大眾收入降低、社會(huì)負(fù)擔(dān)加重、消費(fèi)乏力。
1
行業(yè)數(shù)據(jù)印象
2021年第四季度,日本零售市場(chǎng)年度同比有所回升,但是沒(méi)有企穩(wěn)提升,行業(yè)數(shù)據(jù)印象還是緩慢下降態(tài)勢(shì),百貨店在持續(xù)下降。
2021年10月,日本百貨店銷售與2020年同期增長(zhǎng)2.9%,達(dá)到2019年同期的99.6%,看起來(lái)似乎恢復(fù)到2019年水平,但是2019年10月因消費(fèi)稅上調(diào)到10%,月度銷售同比2018年大幅下跌17.5%,因此這個(gè)數(shù)據(jù)相當(dāng)于2018年的81.6%。客流量同比2020年增長(zhǎng)2.6%,比2019年增長(zhǎng)7.7%,相當(dāng)于2018年的88.6%。
2021年11月、12月合并看,百貨店銷售比2020年同期有所增長(zhǎng),不及2019年。購(gòu)物中心與2020年同期比略有回升,比2019年下降近10%。超市略有下降,便利店、藥妝店基本持平。服務(wù)類型有所提升,受年底忘年會(huì)等習(xí)俗影響,餐飲、旅行、娛樂(lè)類稍顯樂(lè)觀,比2019年仍然呈下降趨勢(shì)。
2022年元旦促銷季節(jié),東京和大阪的主要百貨店的銷售比2021年同期增長(zhǎng)20%至60%,客流量增長(zhǎng)30%至70%。比2020年元旦還處于下降狀態(tài)。2022年1月上半月,三大主力百貨店環(huán)比下降幅度擴(kuò)大,與2019年同比下降10%。
因?yàn)椴煌瑱C(jī)構(gòu)統(tǒng)計(jì)口徑不同,以上引用數(shù)據(jù)僅供參考,不過(guò),各機(jī)構(gòu)數(shù)據(jù)反映的趨勢(shì)相同。
2
直接歸因分析
結(jié)合日本百貨店協(xié)會(huì)的歸因分析,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diǎn):
一是消費(fèi)主力人群老化。使用頻率和消費(fèi)額減少。年輕一代人數(shù)萎縮,多渠道個(gè)性化消費(fèi),加速遠(yuǎn)離百貨店,目標(biāo)市場(chǎng)大幅縮小。首都圈百貨店作為行業(yè)代表,因疫情失去了入境需求,少量高端消費(fèi)增長(zhǎng)難以支撐總體業(yè)績(jī),同樣陷入營(yíng)銷苦戰(zhàn)。
二是消費(fèi)價(jià)值觀趨于成熟。從“物品消費(fèi)”向“事務(wù)消費(fèi)”轉(zhuǎn)移加快,關(guān)注個(gè)性體驗(yàn)、相對(duì)忽略物品感受,二手服裝市場(chǎng)興起。百貨店始終以銷售商品為主,調(diào)整轉(zhuǎn)型緩慢,經(jīng)營(yíng)理念落后于消費(fèi)觀趨勢(shì)。
三是消費(fèi)渠道多元化,消費(fèi)購(gòu)物場(chǎng)景轉(zhuǎn)移。百貨店主要以富裕階層和中老年人階層為主,年輕一代遠(yuǎn)離百貨店,流向品種豐富的購(gòu)物中心。百貨店固守面接待客的優(yōu)勢(shì),網(wǎng)購(gòu)開(kāi)發(fā)延遲,網(wǎng)購(gòu)利用率不到整體銷售額的1%,經(jīng)營(yíng)產(chǎn)品組合落后于數(shù)字化時(shí)尚需求。
可視化(MyEL),是1998年創(chuàng)業(yè)的市場(chǎng)調(diào)查公司,主要是自主組織問(wèn)卷調(diào)查,后來(lái)加上網(wǎng)絡(luò)調(diào)查手段,并將調(diào)查結(jié)果數(shù)據(jù)庫(kù)化,作為社會(huì)第三方,持續(xù)監(jiān)測(cè)會(huì)員企業(yè)所在的業(yè)態(tài)及同行企業(yè)的市場(chǎng)反應(yīng)。
該機(jī)構(gòu)從2006年開(kāi)始監(jiān)測(cè)百貨店的客群光顧頻率變化等指標(biāo),2021年是第七次調(diào)查,具體展開(kāi)時(shí)段是2021年3月1日至5日,采用網(wǎng)絡(luò)調(diào)查方法,有效回答者為10052人。
2021年,顧客對(duì)百貨店看法有什么不同?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光顧百貨店的頻率半年一次以上約45%,每月一次以上的低于20%,其中,隨著年齡增長(zhǎng),女性顧客光顧率較高。 連續(xù)比較看,百貨店的主要活力指標(biāo)——客流量在持續(xù)萎縮。
關(guān)于去百貨店的消費(fèi)內(nèi)容,大約40%是去百貨店地下超市,另外有購(gòu)買(mǎi)點(diǎn)心、特產(chǎn)、禮品等分別占20%左右,去餐飲店、飲食街、國(guó)內(nèi)地方物產(chǎn)展、中元節(jié)日用品等分別為10%左右。購(gòu)買(mǎi)男裝、女裝、時(shí)尚雜貨等各占10%左右。
對(duì)于百貨店的特性評(píng)價(jià),主要魅力特性排在第一位的是“有尊貴高級(jí)感”,排在第二位是“商品質(zhì)量好”。主要不滿意項(xiàng)目排在第一位的是“價(jià)格高”,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排在第2位的“店員啰嗦、麻煩”。調(diào)查結(jié)果,與上述概括分析結(jié)果吻合,顯而易見(jiàn),百貨店自釀的尷尬口碑,還要扛下去。
3
深度觀察分析
第一、二手服裝市場(chǎng)興起
綜合服裝類消費(fèi)趨勢(shì),是觀察零售行業(yè)重要的景氣指標(biāo)。
日本2020年國(guó)內(nèi)服裝市場(chǎng)合計(jì)供應(yīng)34.1億件,其中外套服裝約22.83億件,總體消費(fèi)量約在14億件,積壓剩余50%多。根據(jù)日本環(huán)境省的報(bào)告,供給衣物總重量為81.9萬(wàn)噸,加上過(guò)去購(gòu)買(mǎi)的將要處理衣物在內(nèi),共有78.7萬(wàn)噸要被處置,其中,51.2萬(wàn)噸作為垃圾處置,12.3萬(wàn)噸被回收再加工,15.4萬(wàn)噸被回收轉(zhuǎn)移利用,轉(zhuǎn)移處置包括4.4萬(wàn)噸用于出口,個(gè)人間轉(zhuǎn)賣為2.6萬(wàn)噸,舊服店和跳蚤市場(chǎng)出售的為8萬(wàn)噸,約合3.37億件。釋放的處理品為新品供給量的3.16%,約7200萬(wàn)件。其結(jié)構(gòu)為:品牌商的正品為0.09%,約為205萬(wàn)件,批發(fā)商社接到的退貨3.59%,約8200萬(wàn)件。幾個(gè)因素疊加,嚴(yán)重?cái)D壓季節(jié)新品流轉(zhuǎn)。
服裝超量供給,購(gòu)買(mǎi)不斷萎縮,造成服裝價(jià)格帶不斷下降,慢慢靠近價(jià)格低廉、材料簡(jiǎn)便、甚至中古二手服裝,無(wú)由頭的高價(jià)新品越來(lái)越被冷落,二手服裝市場(chǎng)就這樣由萌芽到逐漸流行。在時(shí)尚的中心地原宿,空置百葉窗店鋪開(kāi)始引入二手服裝店填空,明治大街上也能看到二手服裝店,甚至,高島屋百貨店公開(kāi)展賣采用舊衣服素材加工的新品,以贏得噱頭,池袋西武百貨店直接吸收顧客二手衣服,開(kāi)設(shè)二手服裝專場(chǎng)提供給顧客置換,從中收取服務(wù)費(fèi),換取客流量。
雖說(shuō)是二手貨,因?yàn)橛幸徊糠质切缕忿D(zhuǎn)移過(guò)來(lái),除了部分面向發(fā)燒友的個(gè)性品以外,只有新品價(jià)格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有的高級(jí)品牌套裝售價(jià)只有新品價(jià)格的十分之一,性價(jià)比突出。經(jīng)過(guò)檢查和消毒清洗,對(duì)于普通大眾消費(fèi)者,根本沒(méi)有抵抗力。
2020年,二手服裝服飾(高級(jí)品牌除外)的銷售額比2019年增長(zhǎng)11.1%,達(dá)到4010億日元。從2016年的1869億日元擴(kuò)大了2.15倍,占“服裝及日常用品”零售額的比例從2016年的1.7%,快速增加到2020年的4.6%、2021年的5.5%。按照數(shù)量增長(zhǎng)比例測(cè)算,增長(zhǎng)接近15%。
時(shí)尚街二手服裝店進(jìn)口服裝規(guī)模也快速增長(zhǎng)。到2021年11月,增長(zhǎng)39.5%,全年測(cè)算為8747噸,超過(guò)2005年高峰期的8082噸,進(jìn)口價(jià)格為877日元/kg,與2018年基本持平,遠(yuǎn)遠(yuǎn)低于2001年、2002年左右1500日元水平。2002年主要是面向發(fā)燒友的美國(guó)復(fù)古品,目前的熱潮已經(jīng)超越了發(fā)燒友圈層,擴(kuò)展到了廣泛的大眾客群。
二手服裝店增加,逼迫經(jīng)營(yíng)新品的服裝店周轉(zhuǎn)困難,新店撤退范圍就可能擴(kuò)大,整個(gè)服裝市場(chǎng)渠道周轉(zhuǎn)越來(lái)越緩慢,效率也越來(lái)越低。
第二、網(wǎng)絡(luò)消費(fèi)沒(méi)有侵蝕實(shí)體零售
很多人會(huì)用網(wǎng)絡(luò)零消費(fèi)擴(kuò)大,侵蝕了實(shí)體零售業(yè)績(jī)?yōu)槔碛桑忉寣?shí)體商業(yè)頹敗。
日本的數(shù)據(jù)顯示不是這樣的,網(wǎng)絡(luò)消費(fèi)基本穩(wěn)定,即使在疫情刺激下,也是一度提升然后恢復(fù)到平穩(wěn)狀態(tài),網(wǎng)購(gòu)消費(fèi)額與總體零售之比重沒(méi)有擴(kuò)大。
根據(jù)日本總務(wù)省的家庭網(wǎng)絡(luò)消費(fèi)頻次調(diào)查(2人以上家庭),2019年12月是45.7%,2020年5月為50.8%,2020年12月為54.6%,2021年一直穩(wěn)定在50%至60%之間,沒(méi)有明顯提升。
從日本網(wǎng)絡(luò)銷售占總體零售額中的比重看,2019年為5%左右,2020年達(dá)到7.4%,到2021年10月,一直在7%至8%之間,也沒(méi)有新的突破。
可見(jiàn)疫情的刺激沒(méi)有出現(xiàn)更大的后續(xù)拉升網(wǎng)購(gòu)效應(yīng)。但是,對(duì)零售各個(gè)細(xì)分業(yè)態(tài)的影響,似乎集中在服裝服飾類。
擴(kuò)大分析視野,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中韓跨境電商進(jìn)入日本服飾時(shí)尚業(yè),以突出的低價(jià)和個(gè)性要素吸引日本青年,投產(chǎn)反應(yīng)快,鮮度和靈敏度也壓倒了日本時(shí)尚品牌,據(jù)估算,中韓跨境電商服裝總銷售額,在年輕人的休閑市場(chǎng)中,估計(jì)占比已經(jīng)超過(guò)10%。
根據(jù)NPD咨詢機(jī)構(gòu)報(bào)告數(shù)據(jù),日本2021年體育鞋及相關(guān)服裝消費(fèi)渠道對(duì)比,在網(wǎng)上購(gòu)買(mǎi)金額比2020年大幅增長(zhǎng)8.5%,與2019年相比增長(zhǎng)10.8%,但是,線下實(shí)體店消費(fèi)大幅減少,比2020年增長(zhǎng)0.7%,比2019年下降20.6%。網(wǎng)絡(luò)銷售主要目標(biāo)就是青年群體,這部分外來(lái)跨境競(jìng)爭(zhēng)因素,可能是青年群體遠(yuǎn)離百貨店以及服裝大賣場(chǎng)的重要刺激點(diǎn)。
4
消費(fèi)能力下降是主要因素
一個(gè)國(guó)家大眾的社會(huì)負(fù)擔(dān),大致分為稅收負(fù)擔(dān)和社會(huì)保障負(fù)擔(dān)。國(guó)際經(jīng)合組織成員國(guó)家大眾平均負(fù)擔(dān)為33.5%,負(fù)擔(dān)最高的是丹麥的46.5%,其次是法國(guó)的45.4%,日本國(guó)民負(fù)擔(dān)率是31.4%。在經(jīng)合組織成員國(guó)中屬于負(fù)擔(dān)較低的一類。
但是,結(jié)合家庭具體消費(fèi)結(jié)構(gòu)、收支結(jié)構(gòu)看,問(wèn)題就會(huì)顯現(xiàn)出來(lái)。
從日本政府公開(kāi)網(wǎng)站中查閱,在大眾消費(fèi)結(jié)構(gòu)中,基本食品消費(fèi)無(wú)法持續(xù)降低,于是、相對(duì)恩格爾系數(shù)逐年增長(zhǎng),2005年為22.9%,2019年為25.7%,2020年為27.5%,同食品消費(fèi)相對(duì)應(yīng),服裝、鞋類等選擇性商品消費(fèi)支出比重逐年降低,2005年為4.44%,2019年為3.67%,2020年為3.17%,這個(gè)數(shù)據(jù)簡(jiǎn)明說(shuō)明,日本大眾消費(fèi)結(jié)構(gòu)在退向基本必需品,消費(fèi)活力持續(xù)降低。
日本總務(wù)省面向兩人以上家庭調(diào)查結(jié)果,2020年平均消費(fèi)支出比上年減少5.3%,其中,床品及鞋的支出減少18.9%,教育娛樂(lè)支出減少18.6%。拉開(kāi)時(shí)間軸對(duì)比看,與相比,家庭消費(fèi)的平均消費(fèi)支出相當(dāng)于2000年的87.6%,服裝及鞋類支出降低了45.5%,服裝服飾占家庭消費(fèi)支出的比率從2000年的3.00%下降到2020年的1.86%,大類消費(fèi)品中只有美容化妝品有小幅增長(zhǎng)趨勢(shì)。
那么,家庭收支結(jié)構(gòu)有什么變化呢?
日本多年來(lái)經(jīng)濟(jì)放緩,大眾群體相對(duì)收入減少,平均工資從2000年到2020年減少6.5% ,少子老齡化和服務(wù)效率低下的行政官僚結(jié)構(gòu),導(dǎo)致大眾國(guó)民社會(huì)負(fù)擔(dān)率快速增加,從20 00年的36.0%增長(zhǎng)到2020年的44.6%,再到2021年的46.0%,參考圖示下面折線。而實(shí)際消費(fèi)支出能力持續(xù)減少,從20 00年到2020年,被服、鞋類支出緊縮,從20 00年5.1%減少到2020年的3.2%,大眾的消費(fèi)選擇也不得不從價(jià)格較高的新品流向價(jià)格較低、性價(jià)比較高的二手服裝。
從消費(fèi)稅看,1989年日本實(shí)施消費(fèi)稅,1997年提高到5 %、2014年提高到8 %、2019年提高到10 %,個(gè)人所得稅總體為18.8%,法人部分的所得稅為12.0%、財(cái)產(chǎn)稅為8.2%、消費(fèi)稅19.7%、其他稅0.3%,社會(huì)保障費(fèi)41.1%。 大眾社會(huì)負(fù)擔(dān)的40%多被社會(huì)保障費(fèi)拿走,現(xiàn)狀是政府還要補(bǔ)助一部分。
兩個(gè)感慨:
之一、疫情有影響,但不是關(guān)鍵影響,行業(yè)發(fā)展受到諸多制約,本身結(jié)構(gòu)性因素是主要的內(nèi)在制衡力量,外在的服務(wù)營(yíng)銷形象,是企業(yè)走出泥潭、煥發(fā)生機(jī)的手段之一部分,不能解決根本問(wèn)題。更多地還要從經(jīng)營(yíng)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本身尋求解決方法。
之二、日本零售商業(yè)的不振,提醒閱讀本文的朋友,消費(fèi)者無(wú)力消費(fèi)、缺乏社會(huì)活動(dòng)的欲望和自由度,就要跳出行業(yè)周期,從其他渠道、平臺(tái)尋求生機(jī)。新年度、問(wèn)題依然,甚至更加困難,要向1930年代的思想領(lǐng)軍者胡適學(xué)習(xí),少說(shuō)空話、少談主義,多做實(shí)事、多解決問(wèn)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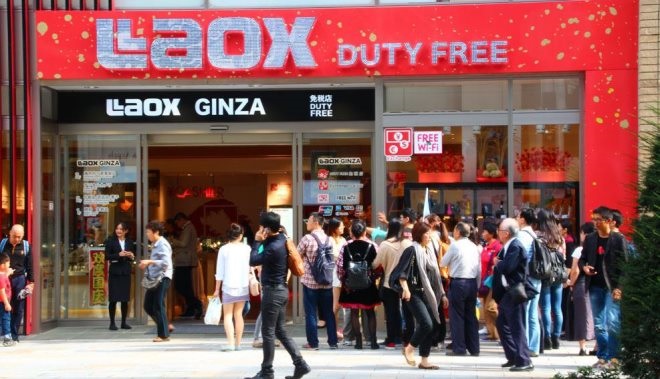


發(fā)表評(píng)論
登錄 | 注冊(c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