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奧賽場現(xiàn)“安踏宇宙”

北京冬奧會的舉辦,帶火了不少體育品牌,安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從開幕式被網(wǎng)友們催著上架的羽絨服同款,到正式項(xiàng)目的比賽服和領(lǐng)獎(jiǎng)服,安踏作為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官方體育服裝合作伙伴,得到了持續(xù)的曝光。
事實(shí)上,安踏借助奧運(yùn)會紅利實(shí)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早有先例。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前后,國內(nèi)運(yùn)動品牌扎堆上市、瘋狂擴(kuò)張,但在紅利消散后,多個(gè)品牌現(xiàn)庫存危機(jī),彼時(shí)的國貨“一哥”李寧也不例外。而安踏卻因?yàn)樘崆爸至闶坜D(zhuǎn)型完成了對李寧的超越,并自此將新“一哥”的位置保持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下國貨與洋品牌正呈現(xiàn)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無論是耐克、阿迪達(dá)斯等運(yùn)動品牌還是優(yōu)衣庫、H&M等快消品牌,在過去的一年都面臨在華業(yè)務(wù)的萎縮,相比之下,一眾新老國產(chǎn)品牌則迎來了供應(yīng)鏈、研發(fā)等全方位的崛起。
這一次,安踏還能把握住時(shí)代的大潮嗎?
安踏旗下多個(gè)品牌現(xiàn)身冬奧賽場,還有超級boss“帶貨”
2月4日晚,第24屆冬季奧林匹克運(yùn)動會在鳥巢體育場隆重開幕,各國的入場儀式成為了羽絨服的大型種草現(xiàn)場。
從加拿大國家隊(duì)身著的Lululemon,到芬蘭國家隊(duì)身著的Icepeak,多國選手的羽絨服被網(wǎng)友們高呼“求同款”。而作為東道主中國隊(duì)的官方合作伙伴,安踏自然也不例外。
開幕式還沒結(jié)束,就有網(wǎng)友發(fā)現(xiàn)了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身上的安踏克萊因藍(lán)羽絨服,并隔空喊話安踏上架相關(guān)產(chǎn)品,甚至有網(wǎng)友涌進(jìn)安踏天貓官方直播間找主播求購。更早之前,中國自由式滑雪運(yùn)動員谷愛凌在社交媒體曬出中國隊(duì)服開箱視頻時(shí),也引發(fā)了廣泛關(guān)注。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些安踏旗下的其他品牌,也借助冬奧會的舞臺展示在了觀眾面前。如始祖鳥的一款羽絨服在不到半小時(shí)的時(shí)間內(nèi),6個(gè)尺寸均被搶購一空,原因是出現(xiàn)了“超級boss同款”。
而截至2月7日,由體育大生意制作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運(yùn)動品牌價(jià)值榜》則顯示,在前三個(gè)比賽日結(jié)束后,斐樂以5金5銀2銅暫居榜首,迪桑特、安踏分別以7、6塊獎(jiǎng)牌數(shù)緊隨其后。

據(jù)了解,這份榜單統(tǒng)計(jì)的是贏得獎(jiǎng)牌的運(yùn)動員或運(yùn)動隊(duì)所穿的比賽服及領(lǐng)獎(jiǎng)服品牌,其他運(yùn)動鞋、運(yùn)動帽、比賽器材等裝備的品牌不納入榜單,當(dāng)獲獎(jiǎng)運(yùn)動員的比賽服和領(lǐng)獎(jiǎng)服為同一品牌時(shí),按該品牌收獲兩面獎(jiǎng)牌來記錄。
榜單前三的品牌均是“安踏系”,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安踏對冰雪運(yùn)動的影響力。
雷達(dá)財(cái)經(jīng)注意到,除了始祖鳥、斐樂(Fila)、迪桑特(DESCENTE)外,安踏旗下的品牌矩陣還包括薩洛蒙(Salomon)、斯潘迪(Sprandi)、可隆戶外(KOLON SPORT)等,涵蓋專業(yè)運(yùn)動、時(shí)尚運(yùn)動、戶外運(yùn)動等多個(gè)差異化受眾群體。
如此龐大的“安踏宇宙”,離不開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以來安踏頻繁執(zhí)行的并購計(jì)劃。以目前公司的財(cái)報(bào)數(shù)據(jù)來看,其中的多個(gè)品牌,已經(jīng)成為了安踏集團(tuán)營收的重要來源。
2009年,安踏在北京奧運(yùn)會的助推下,已經(jīng)將門店擴(kuò)至近6000家,而時(shí)任安踏總裁的丁世忠,展露出了對經(jīng)營高端品牌的迫切愿望。
彼時(shí),市值在200億港元以上的三家中國體育用品公司,李寧有Lotto,中國動向有Kappa,只有安踏并購步伐緩慢。于是丁世忠出手從百麗國際處收購了與Lotto和Kappa同為意大利品牌的斐樂,試圖為公司尋找新的增長點(diǎn)。
起初,這筆交易并不被資本市場看好。發(fā)布收購公告的當(dāng)日,安踏股價(jià)不升反降,畢竟斐樂2008年在中國內(nèi)地和香港還有累計(jì)近4000萬元的凈虧損,且其在意大利本土也已被Kappa和Lotto超越。
但在被安踏納入麾下后,斐樂業(yè)績卻迎來爆發(fā)。浦銀國際數(shù)據(jù)顯示,2015-2020年,斐樂收入復(fù)合增長率達(dá)56%。至2021年上半年,斐樂的營收和經(jīng)營溢利在安踏中的占比已經(jīng)分別達(dá)到了47.5%和53.2%。
或許是有了斐樂的經(jīng)驗(yàn)在前,也或許是為了冬奧會的“五年冰雪戰(zhàn)略計(jì)劃”做足準(zhǔn)備,2017年安踏與北京冬奧組委達(dá)成贊助協(xié)議前后,公司密集收購了日本高端運(yùn)動品牌迪桑特和韓國知名戶外品牌Kolon Sport在大中華區(qū)的品牌業(yè)務(wù),以及始祖鳥背后的母公司亞瑪芬體育(Amer Sports)。
其中,為收購亞瑪芬體育,安踏聯(lián)合方源資本、騰訊等投資者組成的財(cái)團(tuán)所投入的資金多達(dá)360億元,創(chuàng)下了我國服裝及體育用品行業(yè)并購史上的紀(jì)錄。

受此影響,安踏體育在2020年的凈利潤已經(jīng)超越了阿迪達(dá)斯(中國),2021年上半年,其228.12億元的營收也超過了阿迪達(dá)斯(中國)的183億元。
此外,公司市值亦在過去的幾年實(shí)現(xiàn)暴漲,一度超5000億港元。2021年7月,安踏股價(jià)達(dá)到歷史最高點(diǎn),超190港元,若將此節(jié)點(diǎn)與十年前相比,則安踏已成功實(shí)現(xiàn)了十年股價(jià)漲超20倍的成就。
國潮當(dāng)?shù)溃笃放平箲]
對于在冬奧會成功出圈的安踏而言,還有一個(gè)好消息,就是其大力收購國際品牌試圖拓展業(yè)務(wù)的時(shí)機(jī),恰逢國潮的崛起。
英國研究公司Euromonitor數(shù)據(jù)顯示,2020年中國主要運(yùn)動鞋服企業(yè)中,耐克和阿迪達(dá)斯分別以25.6%、17.4%的市場份額占據(jù)前兩位,安踏則為15.4%。相較而言,2016年時(shí)三家公司的市占率為21.2%、16.4%、10.4%。
而在2021年新疆棉等事件發(fā)酵后,耐克與阿迪達(dá)斯等洋品牌的優(yōu)勢更是進(jìn)一步被蠶食。
投資研究機(jī)構(gòu)晨星公司報(bào)告顯示,2021年4月阿迪達(dá)斯、耐克的天貓旗艦店銷售額分別同比下降78%、59%。
根據(jù)耐克方面披露的財(cái)報(bào),2022年第二財(cái)季(2021年8-11月),耐克在大中華區(qū)的營收同比下跌20%,利潤同比下跌36%,大中華區(qū)也成為耐克在該財(cái)季中下滑最嚴(yán)重的地區(qū)。
與此同時(shí),2022財(cái)年上半年(2021年5-11月),耐克整體營收同比增長8%,但大中華地區(qū)營收卻同比下滑6%,成為耐克全球市場中唯一下滑的地區(qū)。其他區(qū)域的同比增長幅度均在10%上下。
阿迪達(dá)斯也出現(xiàn)了類似的情況。2021年上半年,其營收同比增長40%,其中第二季度營收同比增長55%,但在中國市場,其第二季度營收卻同比下降16%,中國市場也成為了公司第二季度唯一收入下滑的地區(qū)。
2021年第三財(cái)季,阿迪達(dá)斯在整體營收同比微增3%的情況下,大中華區(qū)的收入更是少了6億歐元之多,亞太地區(qū)也維持了在所有銷售地區(qū)中獨(dú)自下滑的屬性。
雖然兩家公司都將業(yè)績的下滑歸結(jié)于疫情影響下,東南亞工廠停工造成的供應(yīng)鏈問題,但行業(yè)人士認(rèn)為,線上布局的相對滯后、產(chǎn)品質(zhì)量的下滑以及國內(nèi)消費(fèi)者的抵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了耐克、阿迪達(dá)斯在國內(nèi)市場的“失寵”。
畢竟連2021財(cái)年在大中華區(qū)創(chuàng)下歷史最佳銷量的優(yōu)衣庫,以及H&M、Zara等快消品牌,2021年在大中華區(qū)都經(jīng)歷了業(yè)績下滑、大規(guī)模關(guān)店等情況,而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很難單純用疫情來解釋。
耐克、阿迪在華業(yè)績遇阻,安踏、李寧等國潮品牌卻正愈發(fā)受到消費(fèi)者青睞。
《百度2021國潮驕傲搜索大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到2021年,中國品牌的搜索熱度從45%提升至75%。
過去的一年中,無論是第一梯隊(duì)的安踏、李寧,還是二、三梯隊(duì)的特步、361°、鴻星爾克等品牌,都或多或少因國潮風(fēng)起而受益。
如安踏在2021年上半年?duì)I收、歸母凈利潤分別同比增長55.51%、131.60%;李寧的這兩項(xiàng)數(shù)據(jù)則為64.97%、187.18%。
2021年雙11當(dāng)日,安踏商品總成交額超46.5億元,同比大漲61%,首次超過耐克,成為全網(wǎng)運(yùn)動類產(chǎn)品中銷量最高的品牌,并將阿迪達(dá)斯遠(yuǎn)遠(yuǎn)甩在身后。
此外,河南暴雨災(zāi)情后鴻星爾克直播間刮起的野性消費(fèi)之風(fēng),特步推出的新廠牌XDNA銷量大漲,以及361°在加大對IP聯(lián)名、體育賽事的投入后受到的熱烈反響都體現(xiàn)了國人對國貨的消費(fèi)熱情。
資本市場上,對標(biāo)Lululemon的國內(nèi)瑜伽服飾品牌瑪婭(MAIA ACTIVE),和被稱為“運(yùn)動服飾潮牌戰(zhàn)斗機(jī)”的粒子狂熱(PARTICLE FEVER)都在2021年底完成了C輪億元融資,后者還是由著名機(jī)構(gòu)高瓴創(chuàng)投獨(dú)家投資。

泰合資本副總裁石松源在為中國先鋒街頭服裝品牌BEASTER擔(dān)任財(cái)務(wù)顧問時(shí)曾表示,國貨崛起背后,有社會時(shí)代思潮的影響,也有新媒介、渠道重構(gòu)了產(chǎn)業(yè)鏈的因素。但更為關(guān)鍵的是,中國已建成全球領(lǐng)先的服裝供應(yīng)鏈,這給企業(yè)在效率及性價(jià)比上帶來了不小的優(yōu)勢。
奧運(yùn)紅利退散后,實(shí)力是關(guān)鍵
那么,冬奧會疊加國潮風(fēng)靡,就能讓安踏在短期內(nèi)躋身國際一線品牌嗎?
分析人士認(rèn)為,內(nèi)地體育上市公司針對奧運(yùn)推出的營銷策略,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對公司的產(chǎn)品銷量及品牌形象形成利好,并提升業(yè)績。但長期而言,對公司的發(fā)展并不會有太大的實(shí)際幫助,長遠(yuǎn)發(fā)展靠的還是公司自身的實(shí)力、經(jīng)營理念等資源,而不是短期的事件型刺激。
以2008年奧運(yùn)為例,彼時(shí)安踏之所以能在紅利期消散后脫穎而出,仰仗的是丁世忠提前的布局。
北京奧運(yùn)會前后,體育用品銷量暴增,以至于提起2012年之前的那段時(shí)期,多位行業(yè)人士都感嘆“那時(shí)候賺錢太輕松了,開店就賺錢”。據(jù)媒體報(bào)道,彼時(shí)一些體育服裝企業(yè)的庫銷比(庫存數(shù)量與銷售數(shù)量的比)一度達(dá)到了10以上,而正常范圍僅是3-5。
李寧就因此受到重創(chuàng),2009年其營收超過阿迪達(dá)斯(中國),市場份額也明顯領(lǐng)先包括安踏在內(nèi)的其他國內(nèi)運(yùn)動品牌一個(gè)檔次,但從2011年開始,李寧的業(yè)績一路下滑,后被安踏全面超越。
特步CEO李冠儀指出,安踏之所以能從這波庫存危機(jī)中幸存,源于丁世忠向阿迪達(dá)斯、百麗、達(dá)芙妮等多個(gè)國際企業(yè)學(xué)習(xí)到的零售變革經(jīng)驗(yàn)和安踏2012年早于一眾國內(nèi)品牌開始的轉(zhuǎn)型。
而丁世忠則將零售轉(zhuǎn)型的成功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為四點(diǎn):一是通過信息化實(shí)現(xiàn)全國大部分安踏專賣店的信息統(tǒng)一;二是由過去的加盟商訂貨改為單店訂貨;三是把零售標(biāo)準(zhǔn)覆蓋到全國每一家店;四是帶著高管走遍中國所有的地級市,了解終端的各種問題。
不過,這四板斧并不能讓品牌一勞永逸。近年來,以安踏為首的國產(chǎn)品牌在經(jīng)營過程中還暴露出了許多新問題。
鞋服行業(yè)品牌管理專家、上海良棲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jīng)理程偉雄認(rèn)為,國貨品牌在產(chǎn)品研發(fā)、品牌傳播創(chuàng)意、運(yùn)動功能等方面與國際品牌仍有差距,要認(rèn)清這一事實(shí),并長期投入。
僅就研發(fā)投入而言,2020年,安踏的研發(fā)支出8.71億元,研發(fā)投入占比僅2.45%,尚不及研發(fā)占比4%的361°和2.7%的特步,比之常年維持在7%以上的耐克、阿迪更是相去甚遠(yuǎn)。
此外,在國際化方面,安踏的海外收入始終是個(gè)謎。盡管在2018年就完成了對亞瑪芬體育的收購,但在財(cái)報(bào)中,公司一直未對國際業(yè)務(wù)有詳細(xì)描述。類比李寧來看,其2021年上半年在中國區(qū)外的收入僅有1.22億元,占總營收的1.2%。足見本土品牌出海之難。
在此背景下,2020年8月,安踏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主品牌的DTC轉(zhuǎn)型,將原本線下分銷商運(yùn)營的門店(約35%近3500家門店)轉(zhuǎn)型為直營模式。簡而言之,就是去除掉生產(chǎn)企業(yè)和消費(fèi)者之間的中間商環(huán)節(jié)。在疫情之前,這種模式在國外頭部運(yùn)動或休閑服飾公司中就已被廣泛采用。
對于DTC戰(zhàn)略成果,安踏體育方面表示,相關(guān)的經(jīng)營數(shù)據(jù)會在2022年3月公布。但目前可以披露的是,電效、商品管理效率、組織效率、盈利等指標(biāo)均有提升。
丁世忠表示,未來10年,安踏集團(tuán)將始終堅(jiān)持“單聚焦、多品牌、全球化”新戰(zhàn)略,2025年安踏集團(tuán)流水目標(biāo)雙千億。以2021年截至目前的業(yè)績來看,這或意味著在接下來的三年,安踏要實(shí)現(xiàn)業(yè)績翻倍。
丁世忠的宏愿能實(shí)現(xiàn)嗎?雷達(dá)財(cái)經(jīng)將繼續(xù)關(guān)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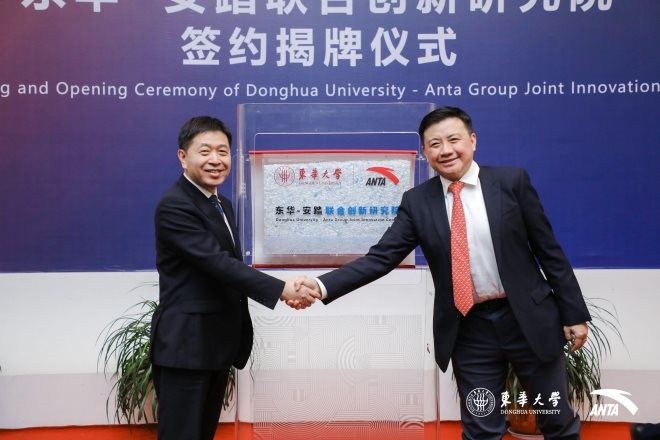
發(fā)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