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商業人:回家過年是一種幸福

來源/聯商專欄
撰文/方湖
回家過年,回老家過年,回農村過個活色生香的煙火年,是一種幸福的期盼。
2022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驚濤駭浪,波瀾壯闊,有驚無險。
疫情阻隔了三年,這三年親人家人聚少離多,甚至都沒有機會見面,也是放棄“過年”的三年。
動態清零之下,疫情封控了十一個月,在12月份疫情管控放開了,本是喜大普奔,迎接老百姓的卻是大面積感染和群體免疫。很多商店和企業因為員工大面積感染,被迫暫停營業,對經濟和生活造成一段時間巨大影響。很多高校陸續開始提前放假,后來是中小學,全國大中小學生提前一個多月進入漫長的寒假假期。
商店關門,企業關門,學校提前放假,給今年過年預留更多富裕的時間。疫情三年,看了太多生離死別,經歷了太多悲歡離合,在經歷相對較低致命性奧密克戎病毒后,有更多時間讓大家靜下心感悟人生。在時間和空間都允許的可能性之下,經歷三年等待,回家過年成為大家不約而同的迫切期待。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二十余年前,我剛從大學走向社會,從政府下海后第一份工作到蘇州打工。那時候做很基層工作,工資收入也很有限。記得那是2001年過年,回到老家口袋不過幾百塊,過完年返程路費還是老媽塞給我的六百塊賣棉花的錢。中間二十余年,除了幾年特殊原因,大多數都是回老家過年的。尤其是2007年媽媽過世后,更是覺得“子欲孝而親不在”的痛心遺憾。
為什么回家過年?
有家的地方沒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沒有家。
家鄉,是我們的根,是我們的血脈,是我們文脈和人情世故所在。那里有我們的鄉音,有我們小時候的回憶,有養育我們的父母和一方水土。
小孩子都盼著過年,因為以前只有過年才能穿上新衣服、吃上好吃的。現在流浪在外的成年人盼著過年,因為只有過年才有時間回老家,看看皺紋更深的爸媽,盡盡孝心。
回家過年是辛苦而幸福的。
回家路程很遠,時間很長,回家是辛苦的。回到家里,給爸媽帶點新鞋和新衣,給孩子們帶點禮物;回到家里,給老房子打掃衛生,添置家具,為房前屋后整理清掃;回到家里,為家里、廚房里,添加年貨和柴米油鹽;過年守夜,給長輩拜年、走親訪友。付出很多,可能更加辛苦,卻是滿滿的幸福。
過年回家,春節大遷移是一個巨大春運工程。從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從南方發達城市到北方城市,形成一個龐大的、浩浩蕩蕩的動態交通網絡。航運、鐵路、公路,飛機、高鐵、綠皮火車、私家車、大巴,甚至摩托車,組成浩浩蕩蕩的回家大軍。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不管今年什么樣收成,回家過年的心情是一樣的。
留給我們過年的時間很短、很短,扣除來回行程,少的甚至不到七天,有的多點也就十余天。臘月二十幾開始陸續從工作地回家,為的是大年三十一頓團圓的年夜飯,或許是全家人圍在一桌熱氣騰騰的飯菜,或許是爸媽和長輩親戚的寒暄絮叨,鄉音、鄉親、與血脈交織的融入,這仿佛宣告辛苦打拼一年的結束,為已經過去的一年劃上一個大大的句號,為即將開始的一年定下新基調、暢想新未來。一個儀式,簡單而純樸,圍桌飲酒,圍爐煮茶,就像一杯老酒越陳越香,越陳越值得回味。一杯酒,仿佛就是一段歷史,一碗茶,似乎就是一個故事,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故事和未來,自己的情感回歸和理想蟄伏。
生活在繼續,年復一年。我們用年來劃分時間段,年不僅是一個時間單位,更用年做為一個儀式,來告別過去、迎接未來,鞭炮煙花熱烈絢爛,各種烈酒的杯觥交錯,茶水的群聚絮叨,拜年后長幼有序的親情互動,各式各樣不盡相同,是一種歡快、是一種灑脫、是一種回歸。
過兩天就是除夕了,我買好了煙花,買好了糖果煙酒,滿載一車子,行駛四百余公里,就可以回到老家,和家人聚在一起,在老屋過個其樂融融的中國年。
歸心似箭,回家過年,過個幸福團圓年。農村過年,有一種煙火味,有一種鄉土味接地氣。用一種傳統而固有的方式,洗去一身塵埃和病毒,迎來全新的一年,充滿轉折與機遇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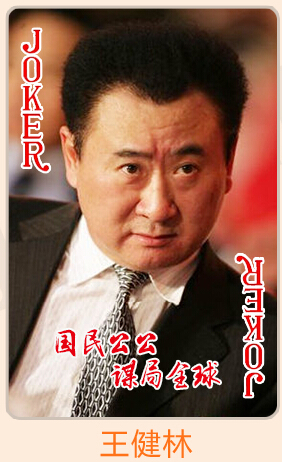


發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