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大戰(zhàn)“消失”的它!

出品/即時劉說
撰文/劉老實
當美團與京東圍繞即時零售、品質外賣、騎手保障等話題展開拉鋸戰(zhàn)時;京美外賣大戰(zhàn)這個被資本精心編排的商戰(zhàn)劇本里,唯獨缺少了一個本該重要的角色——那個曾與美團平分秋色的藍色圖標,此刻正蜷縮在阿里生態(tài)的角落,任憑輿論浪潮沖刷卻激不起半分水花。
雖貴為行業(yè)二當家,但在這期間,餓了么既未推出顛覆性的戰(zhàn)略舉措,也未在輿論場中發(fā)出強有力的聲音,且完全看不出這是餓了么有意在隔山觀虎斗,而是因其長期戰(zhàn)略困局導致的必然結果。
被預設的戰(zhàn)場:京美交鋒中的角色缺位
春節(jié)前的劉雯硬鋼美團事件像一劑催化劑,將后者推至輿論風暴中心。這場由騎手權益引發(fā)的公關危機,卻成為春節(jié)過后京東高調入局外賣市場的絕佳跳板(梳理下來,很難不讓人懷疑從劉雯開始就是一場被后背資本寫好劇本的商戰(zhàn)連續(xù)劇)。京東外賣以“品質堂食0傭金入駐+為騎手交社保+百億補貼”組合拳高調登場,上線40天日訂單突破百萬,而美團則用“向餐飲投入1000億”與“美團閃購獨立”上線反擊。
雙方在社交媒體上的隔空喊話、高管互嗆,儼然上演著一場預先編排的戲劇。不過在這場雙雄爭霸的劇本里,餓了么的沉默顯得格格不入——即便其背靠阿里日均仍有千萬訂單,市場聲量卻已跌至冰點。
實際上這種沉默早有預兆。2024年雙十一期間,當美團聯(lián)合名創(chuàng)優(yōu)品推出“30分鐘送達爆品專區(qū)”,餓了么仍在重復著“滿減”的陳舊套路;當京東以“咖啡+手機”的混合訂單驗證高頻打低頻邏輯時,餓了么與盒馬的協(xié)同配送依然停留在PPT階段。
這不得不讓人擔心,美團和京東圍繞外賣和即時零售的大戰(zhàn),或許真正的受害者會是餓了么!
在商戰(zhàn)史上,依靠隔代創(chuàng)新降維打擊行業(yè)巨頭的案例雖然不在少數(shù),比如蘋果的智能機直接讓把當時的行業(yè)二霸諾基亞和摩托羅拉秒成了渣,但再無這種斷崖式優(yōu)勢前提下,往往都在上演著兩虎相爭傷及第三者故事。
比如那個經(jīng)典的涼茶雙雄對決案例。2012年廣藥收回“王老吉”商標后,加多寶被迫更名,雙方圍繞紅罐包裝、廣告投放、渠道資源展開全面對抗。王老吉依托國企資源搶占央視黃金時段,加多寶則以“全國銷量領先”的廣告話術強攻終端,兩年內合計投入超50億元廣告費。這場戰(zhàn)爭導致涼茶行業(yè)利潤率從25%驟降至10%,最慘的是原本行業(yè)老三的和其正因無法承受廣告轟炸與價格戰(zhàn),市場份額從10%萎縮至2%,最終退出主流市場。
再比如2015年,滴滴與快的在騰訊和阿里支持下展開瘋狂補貼戰(zhàn),日均燒錢超4000萬元,迅速占據(jù)國內90%市場份額。Uber中國雖憑借技術優(yōu)勢短暫獲得15%份額,但面對滴滴快的的渠道壟斷與資本壓制,最終在2016年以10億美元現(xiàn)金+滴滴17.7%股權的代價被收購。這場“三國殺”中,Uber中國的退出標志著本土巨頭對國際玩家的全面勝利,也為后續(xù)滴滴壟斷市場埋下伏筆。
外賣市場同樣在8年前也上演過經(jīng)典商戰(zhàn)。2017年,美團與餓了么在外賣市場展開“千團大戰(zhàn)”,雙方通過紅包補貼、騎手爭奪等手段將市場份額提升至85%。百度外賣雖憑借白領市場差異化定位一度占據(jù)15%份額,但在百度戰(zhàn)略收縮與阿里注資餓了么的雙重壓力下,最終以8億元賣身餓了么。
此外,包括安卓iOS聯(lián)手埋葬Windows Phone、ofo摩拜血拼拖垮第二梯隊、攜程去哪兒合并終結途牛、可口百事圍剿非常可樂、58同城趕集網(wǎng)吞并百姓網(wǎng)等等。
這些案例揭示了商業(yè)競爭的底層邏輯:當行業(yè)進入成熟期,行業(yè)大佬們的競爭往往演變?yōu)橘Y源消耗戰(zhàn),第二梯隊若無法在細分領域建立護城河,終將成為巨頭博弈的犧牲品。企業(yè)的生存之道,在于要么成為生態(tài)構建者,要么在巨頭尚未完全覆蓋的領域建立不可替代性。
失血的雙翼:戰(zhàn)略搖擺與生態(tài)困局
餓了么創(chuàng)立于2008年,早于美團外賣(2013年)五年,曾是外賣行業(yè)的拓荒者。2015年,餓了么以33.7%的市場份額位居第一,美團僅占23.1%。
然而,2016年,美團采取“農(nóng)村包圍城市”戰(zhàn)略,率先攻入餓了么尚未覆蓋的二三線城市。餓了么卻錯誤判斷市場趨勢,認為只有一線城市適合外賣業(yè)務,導致在下沉市場的布局嚴重滯后。就這樣,美團通過地推鐵軍搶占下沉市場,疊加高頻補貼,2018年反超餓了么,市占率突破60%。
當美團早在2018年就開始布局美團閃購業(yè)務,并在2025年實現(xiàn)非餐飲品類日訂單量突破1800萬單時。這邊的餓了么直到2024年才啟動“優(yōu)店騰躍計劃”,投入10億元支持商家數(shù)字化,但此時美團已建立起顯著優(yōu)勢。
當美團通過“拼好飯”等創(chuàng)新業(yè)務實現(xiàn)增量,而餓了么的“特團”業(yè)務卻未能復制成功。2024年,美團“拼好飯”日均單量接近500萬單,成為重要增長極,而餓了么的同類業(yè)務卻反響平平。
阿里對餓了么的"庇佑",某種程度上成了束縛其翅膀的金絲籠。2018年收購時,95億美元的天價彰顯著阿里制衡美團的野心,但七年后回看,這卻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并購史上最昂貴的教訓之一。
那時候阿里對餓了么的資源傾斜不可謂不慷慨:支付寶首頁入口、88VIP會員互通、高德地圖導流……
而被并入阿里生態(tài)的餓了么,既要承接支付寶流量,又要協(xié)同高德地圖、飛豬旅行,最終演變成“四不像”,這種“強管控”同時也削弱了餓了么的獨立性。例如,阿里要求餓了么與口碑合并為“本地生活公司”,導致戰(zhàn)略重心從外賣轉向全場景服務,但這一布局并未形成合力,反而因組織架構冗余拖累效率。
反觀美團,王興堅持“無邊界擴張”,從外賣延伸至到店、酒旅、即時零售,構建了“高頻帶低頻”的生態(tài)閉環(huán)。而餓了么的定位卻在本地生活服務的迷宮中不斷迷失。
這種戰(zhàn)略混亂在組織架構上暴露無遺。2023年阿里分拆后,餓了么被劃入的“生活服務板塊”本應形成協(xié)同效應,實則陷入資源爭奪的怪圈:高德專注出行,飛豬深耕旅游,而最需要流量灌溉的外賣業(yè)務,反而要為其他板塊導流。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團即便在拓展共享單車、社區(qū)團購等新業(yè)務時,始終保持著“外賣為核,多元輻射”的戰(zhàn)略定力。2024年財報顯示,美團核心本地商業(yè)營收占比達78%,其中外賣業(yè)務貢獻超50%流量入口,這種“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的生態(tài)構建能力,恰是餓了么最欠缺的。
再加上阿里系職業(yè)經(jīng)理人取代了張旭豪團隊,五年內更換三任CEO,導致戰(zhàn)略連貫性喪失。餓了么原有的創(chuàng)業(yè)文化與阿里的“中臺化”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導致執(zhí)行效率低下等等,都折射出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的殘酷法則:沒有永恒的巨頭,只有不斷進化的生態(tài)。
褪色的藍軍:從創(chuàng)新先驅到模仿囚徒
回望2015年,張旭豪帶領的餓了么團隊曾用“蜂鳥系統(tǒng)”顛覆傳統(tǒng)配送,開創(chuàng)分鐘級送達先河。但如今打開餓了么APP,從界面設計到促銷玩法,處處可見美團的影子:美團推會員體系,餓了么跟進;美團上線“準時寶”,餓了么推出“準時達PLUS”;美團推出“神搶手”直播頻道,餓了么就上線“爆品直播間”;美團試點透明廚房,餓了么便跟進“明廚亮灶”計劃;甚至美團的頁面設計、營銷活動也成了餓了么的“模板”。
這種亦步亦趨的模仿,甚至蔓延至組織架構——2024年餓了么設立的“戰(zhàn)時指揮部”,與美團七年前的“沖鋒隊”模式如出一轍。
更深層的危機在于創(chuàng)新能力的衰竭。當抖音以“內容+算法”重塑到店消費場景,京東用自營物流重構配送體驗時,餓了么的“殺手锏”仍是阿里的資金輸血。
2024年Q1財報顯示,阿里向餓了么注資超30億元用于市場補貼,但用戶增速仍落后行業(yè)均值5個百分點。這讓人想起王興多年前的論斷:“靠錢燒出來的市場份額,就像沙灘上的城堡。”
當然,京東的入局或許難以撼動美團的霸主地位,但足以成為壓垮餓了么的最后一根稻草。京東外賣上線以來,不僅美團,包括很多餓了么的存量用戶也被直接搶奪。這種“虎口奪食”的戲碼背后,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殘酷現(xiàn)實:美團和京東的較量,本質上是兩種商業(yè)邏輯的碰撞——美團的“超級APP生態(tài)”與京東的“品質供應鏈”。而仍在單一維度競爭的餓了么,如若不能在這兩者之間找到第三條道路,或將徹底淪為行業(yè)的“背景板”。
這個春天,美團閃購獨立運營的新聞占據(jù)所有財經(jīng)頭條,京東外賣的紅色旋風席卷城市街頭,而那個曾經(jīng)改變中國人餐飲方式的藍色圖標,正緩緩沉入互聯(lián)網(wǎng)記憶的深潭。餓了么的“消失”不僅僅是外賣市場的話語權,更是商業(yè)文明迭代的必然——在這里,沒有永恒的王者,只有永恒的創(chuàng)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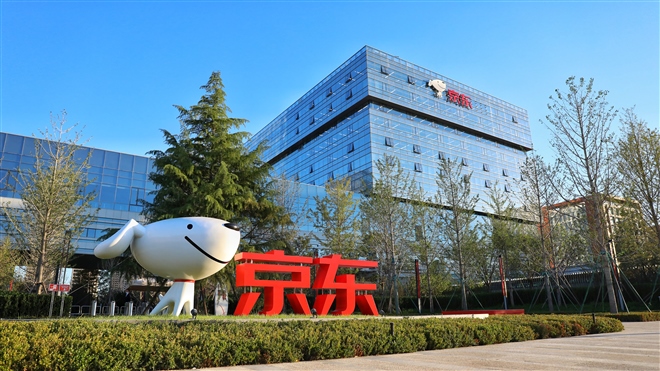


發(fā)表評論
登錄 |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