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鮮電商“最后一公里”的迷局
出品/聯商專欄
撰文/聯商專欄、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業態市場專委會委員 王瑋
最早的中心地理論提出消費者為了單目的購物會選擇去最近的商場。這個看似非常簡單直白的觀點其實蘊藏著深奧的大道理,一直都在影響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商業模式的演變。特別是對于全球行業都在關注和熱議的“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本文擬從中心地理論的基本概念到運輸網絡對于零售的重要作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迷局從本質上講清楚這個問題。
1. 中心地理論的限程和門檻概念
1933年,德國地理學家泰勒出于對城市為什么會大小不一的好奇和研究,通過零售發現了城市與其更遠的腹地之間的經濟關系。泰勒認為人們聚集在城市里是為了分享商品和思想,中心地的存在純粹是出于零售的經濟目的。所謂中心通常都聚焦區域的商業中心,中心地帶的存在就是為了向周邊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務。因此,城市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分銷中心的網絡。
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中包括了限程和門檻兩個重要變量。限程是指消費者為了獲得商品或服務可以去達的最遠距離;門檻是指中心地商場為了維系生存所需要覆蓋的至少所需消費者的數量。所以中心地理論作為城市空間規劃的一個具體運用就是擬定商場規模的大小和商圈輻射的范圍。
泰勒用低階商品(Low Order)和高階商品(High Order)的概念進一步說明。所謂低階商品就是每日必需的商品,比如生鮮食品和快消品等。由于人們需要經常購買這些物品,小的區域比如鄉或鎮上的較小商場就可以滿足周邊居民日常的就近購買需求,而不必車馬勞頓地去到更遠更大城市的中心地商場;而高階商品則是指相對耐用的消費品,比如像汽車、家具、珠寶和電器等商品。這些商場要求的門檻比較高,需要輻射大量的人群。因為人們對這類商品的購買頻次較低,這類商品的商場在人口較少的區域難以維系生存。因此,這些商場的購物限程都較大,往往位于更大城市的中心地帶。
泰勒提出中心地理論把不同的中心地分為了村、鄉、鎮、市和都市5個層級。如果用今天已經高度城市化的零售語言描述就是超區域型、區域型、次區域型、社區型和鄰里型的商場。美國和澳大利亞直接把社區和鄰里型的購物中心稱為超市型購物中心。所以,在一個城市中,一定是由少數大型商場和為數不太多的中型商場加上為數眾多的小型商場按類似于寶塔形狀的分形層級分布。
銷售高頻低價的超市因為距離消費者較近,數量也相對較多。而相對低頻高價的中、大型商場的數量就會少很多(但國內情況正相反,但這不是本文敘述的要點,本文的重點是講購物限程和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泰勒在提出消費者為了單目的購物選擇去最近的商場時候還做了經濟度量的平衡分析,即這時消費者對于他/她所購商品的價值等于商品的價格加上消費者的購物旅行的出行成本:
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格+出行成本
因此,出行成本其實就構成了泰勒提出的“購物限程”的概念。由于20世紀30年代的運輸技術和交通條件的限制,消費者一般很難去到很遠的商場購物。商場的規模(門檻)自然也不會太大。但是,隨著后來汽車的普及和道路的改善,人們的機動性極大地增強,出行的時間和成本也都大大降低,這無形中擴大了消費者的“購物限程”的距離,也為零售商進一步提高中心地商場的規模(門檻)提供了契機。
2. 不容忽視的運輸技術對于零售發展的巨大貢獻
由中心地理論可以理解,任何商場或任何零售模式本質上都是商品的信息網絡和貨品的運輸網絡的統一和疊加。消費者首先需要通過信息網絡知道商品,然后才能通過運輸網絡得到貨品。信息網絡可以是實體的,比如食品雜貨店和超市;也可以是虛擬的,比如那個年代分布在美國千家萬戶的西爾斯商品的目錄。消費者通過親自到店的搜尋和購買并自提回家完成了這兩個網絡的交融和閉合;消費者也可以在家搜索商品目錄,通過電報或信件訂購并通過郵局將貨品郵寄到消費者的家中,從而完成了這兩個網絡的交融和閉合。從消費者對商品的價值和購物限程的成本判斷,中心地其實就是商品的信息網絡和貨品的運輸網絡在零售商和消費者之間相互交融形成的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也是由中心地的區位、消費者的距離以及商品的特性等要素共同決定的。
消費者對于早年的步行5到15分鐘的距離,或者后來可以開車或乘坐公共交通5到15分鐘可以達到的距離的所需時間和出行成本其實是不太介意的。如果用中心地理論中的消費者對商品的價值判斷公式(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格+出行成本)解釋,這時消費者對出行成本的考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人類有天生外出的喜好和社交互動的需求。小動物和小孩子天生喜歡到戶外的環境玩耍,零售提供了社交互動的體驗,購買可以感受勞動收獲后消費的滿足感。人類這種天生的心理因素結合運輸技術的進步帶給消費者的機動性的增強,為零售模式的發展和演變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我們可以用步行10分鐘約600米和開車10分鐘約3公里的購物距離做一個比較。這里600米和3公里并不僅是長度放大5倍的問題,而是以中心地作為商圈圓心延伸的半徑。所以按圓面積的平方計算,開車10分鐘的商圈覆蓋面積是步行10分鐘的25倍之多。加上開車的人相較于步行者的手提購物可以做更多的購買,假設就按多一倍計算,這個25倍就可以輕松變為50倍。注意根據零售的中心地理論這個“購物限程”的擴大和“零售門檻”的提高都是源于運輸技術進步的汽車的普及和道路的改善,是運輸科技使消費者擁有主動的機動性對于零售的巨大貢獻。這也解釋了20世紀主要零售模式經歷了從較小的食品雜貨店到超市,到大型超市和品類殺手再到購物中心的演變。從1935年到1982年間,美國的食品雜貨店的數量從40萬家減少到16.2萬家,而超市的數量從386家增加到了26640家。根據美國購物中心協會的統計,美國的購物中心總數在2018年達到了114915家。試問信息技術對于零售的提升有這樣明顯嗎?所以,我們不能以為只有信息技術才能促進零售的變革和進步,而無視運輸技術的巨大貢獻。
3. 最后一公里的迷局
我們可以把迷局可以比喻為迷宮,內部通路復雜難辨,人進去后很不容易走出來的建筑物。充滿著不易直接察覺的奧秘,所謂“最后一公里”的迷惑可以有以下三點:
第一,忽視并扼殺了這種由于運輸科技進步帶給消費者的主動機動性對于零售的巨大降本增效的作用;將消費者被動地置于家中,還幻想著要實現比原本已經擴大了50倍的更大的銷售額,卻不曾想到你還必需為這個已經放大了50倍以上的市場的運輸成本買單。
第二,因為“前置”實際已經非常接近消費者,所以能夠真正帶給消費者價值提升的空間有限。零售購物可以滿足人類天生喜好外出和追求互動的體驗;去商場購物原本就是一件享受的事情,而且外出的社交活動,呼吸新鮮空氣和走路鍛煉還有益于身心健康。這也是為什么國內85%以上的消費者依然選擇到店購買(根據艾瑞咨詢的報告)。15%的生鮮電商的滲透率就是一個天花板。在仲量聯行最新發布的2022年全球超市報告中引用了美國生鮮電商銷售占比的一個走勢圖(圖3-1)。分析顯示美國的情況也非常類似。除了疫情肆虐的2020年,生鮮食品的網上銷售突破50%以外,一切都已經回歸到15%的正常范圍。而且通過這次疫情大家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更清楚的認識。
圖3-1 美國生鮮電商銷售及占比走勢圖
第三,生鮮類產品的極易腐蝕和損耗的特性極大地增加了運輸的難度、成本和風險,也無形中增加了整個供應鏈系統和超市營運的復雜度和不確定性。借用原阿里巴巴CEO衛哲先生的定義,生鮮食品應該屬于“電商的非友好型商品”。
在仲量聯行最新的2022全球超市的報告中提到了幾家食品快遞的初創企業都在2022年調整并收縮了發展計劃。經過數年前的快速擴張,像Gopuff、Buyk、JOKR和Fridge等這些美國人稱之為“幽靈雜貨店”都通過前置的微型倉庫為消費者提供不到15分鐘的訂單配送服務。盡管也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風險投資,但這類公司的發展并不如意。2022年3月,Buyk根據破產法第11章申請破產,結束了芝加哥和紐約市39家門店的運營。(俄羅斯投資背景的Buyk自然可以把原因歸咎于俄烏戰爭,其實2022年2月24號才開始的俄烏戰爭與Buyk的破產沒有關系。就像很多企業把破產或下行歸咎于疫情也是一樣)。JOKR關閉了美國的業務,Gopuff也縮小了倉庫規模……
同樣的情況讓人想到了國內的每日優鮮和叮咚買菜等,還有盒馬的30分鐘無冷鏈送貨到家的服務其實就是把消費者原本一周一次性約400~500元的購買分散在了每天的70~80元之間。零售額并沒有因為這個創新的服務獲得飛躍式的提升。根據中心地理論的交通成本,盒馬不僅貼補了消費者的出行時間和交通成本,甚至還貼補了消費者的儲藏成本,因為消費者家中都不再需要大冰箱了。不過盒馬的情況還是要好過每日優鮮和叮咚買菜,因為盒馬還開放消費者到店的服務,所謂“倉店一體模式”加上盒馬在自主品牌、會員制和連鎖經營這些傳統零售經營方式上的用心,這在較大程度上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那些“盒小馬”或“盒馬里”的創新如果不是以吸引消費者到店為目標一定會事與愿違。原因也非常簡單,越是靠近消費者,這種“到家”的服務就變得越扭曲。近日雖然看到盒馬鮮生開始盈利和叮咚買菜也獲得階段性盈利的消息,考慮到2022年國內極度的封控情況,國內生鮮電商的滲透率也不過如此(遠不及美國)。所以,看一下美國生鮮電商疫情后的走勢,我們遠沒有到可以為這些新零售歡呼的時刻。
仲量聯行在這份超市報告中并沒有對這些“幽靈雜貨店”的失敗給出確切原因。只是提到了市場對微型倉庫的懷疑和缺乏吸引力以及租金上漲等令人擔憂的因素。但筆者認為,關鍵的原因通過中心地理論的購物限程和零售門檻的概念,加上零售的兩個網絡屬性的特點的認知很容易幫助行業看清問題所在。這些企業在高估信息技術對于零售貢獻的同時,忽略了運輸技術對于零售的關鍵作用(如上面舉例說明的至少25~50倍的效力提升)。原因就是將電商與實體割裂看待,把不可或缺的零售的運輸網絡和信息網絡分離。真的以為有朝一日,電商可以取代實體,而不知道這些實體商業正是因為運輸技術的提升和消費者機動性的加強為實體商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擴容和增長的機會。
在這方面,英國的John Lewis百貨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示。John Lewis作為一家英國的連鎖百貨和超市企業很早就實施線上和線下并舉的經營戰略。但是,John Lewis并沒有像很多企業那樣在O2O的線上燒錢,而是重點投資和改善物流系統。John Lewis推出的“Click and Collect” 服務舉措可以讓消費者網上下單店內取貨。(注意是消費者到店取貨而不是配送到家。配送到家也是可以的,但消費者需要支付額外的運費。這部分占比不到1%)。結果,2013年John Lewis的線下實體銷售保持了2%的穩定增長,而線上的銷售為John Lewis帶來了40%的額外增長,交出了一份令全球零售商羨慕的答卷。2021年John Lewis的線上訂單已經占到了John Lewis總體銷售額的67%,其中生鮮品類的占比僅為16%。關鍵是John Lewis在實施零售創新的同時知道維護消費者到店的心理需求和利用消費者主動到店的機動性的重要意義。這種機動性對于在零售的信息網絡和運輸網絡的交融和互動中保持平衡至關重要。所謂中心地其實就是零售商和消費者之間的心理和地理之間的平衡點。
至此,本文從理論解釋和事實證明對生鮮電商的最后一公里做了剖析。“最后一公里”需要填補的窟窿巨大,其中既有隱形的消費者的心理和行為習慣,也有半隱半顯的因為消費者到店對于零售降本增效的巨大作用(不利用則成為巨大的屏障),還有顯性的因為商品性質而帶來的運輸和營運的風險、復雜度和不確定性。這些都是消費者對“最后一公里”并不買單的關鍵原因所在!
零售創新一條不變的原則就是要在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務的同時做到降低成本。千萬不要以為只是信息技術在驅動零售變革,從而落入巨大的運輸成本黑洞。所以,奉勸那些陷入“最后一公里”迷局的人們迷途知返吧。
參考文獻:
[1]王瑋.商業地產決策理論和戰略實踐 [M].北京:中國建筑出版社,2022.
[2]Nicolas Lau: Grocers grow formats big and small [R]February 2023
[3]Chloe Rigby: Online sales drives strong sales growth at John Lewis despite store closure, Waitrose sales fall slightly while pre-tax losses narrow [R]March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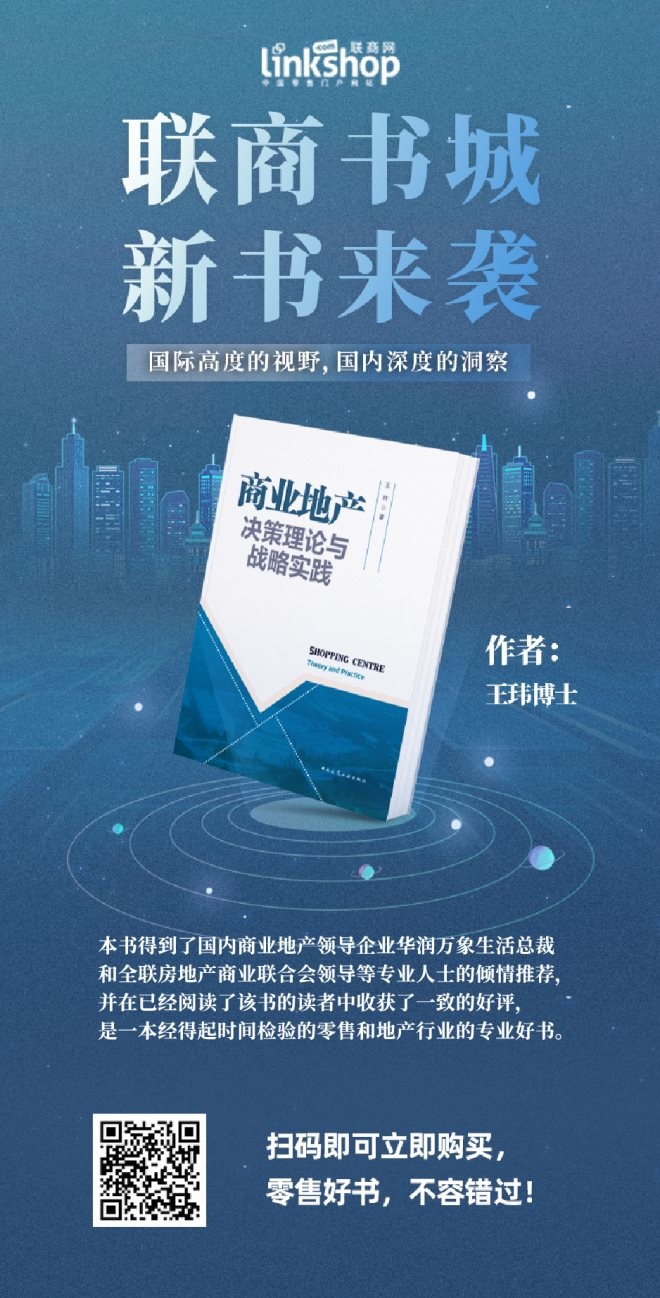






發表評論
登錄 | 注冊